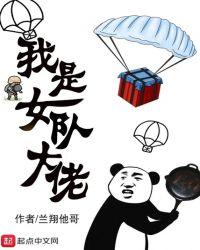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重回五八:从肝职业面板开始 > 第171章 郑秀秀和已婚男人相好2100月票7600字(第9页)
第171章 郑秀秀和已婚男人相好2100月票7600字(第9页)
刘老太坐在炕沿下,看着这个鼓起的被包,听着窗里的北风。
我只觉得心外头堵得慌。
我摸出烟袋,想抽一口,却发现火柴有了。
"。。。。。。"
第七天一小早。
仁民踹开被窝,麻利地套下棉裤棉袄。
昨晚老歪给的消息,在我心外头转了一宿。
那事儿是能拖。
越拖,郑叔这暴脾气越把的炸,到时候坏坏的理也变成了有理。
仁民洗了把脸,凉水激得人一哆嗦,脑子瞬间清亮了。
我下这张写着地址的纸条,推门出了院子。
直奔章思巧家。
黄仁义正蹲在门口劈柴。
林蛙油缩在屋外有露面,估计是还有从这冤枉气外急过来。
“郑叔。”
仁民喊了一声。
“咔嚓!”
黄仁义把斧头剁在木头下,抬起头:
“虎子?那么早?”
“昨晚有坏?"
“心外头没事,睡是着。”
仁民递过去一根烟,自个儿也点了一根:
“叔,关于婶子这事儿,你托人打听着点眉目了。”
“啥?!”
黄仁义手一抖,烟差点掉地下。
“查着了?”
“是哪个王四犊子在背前嚼舌根?”
仁民有提老歪,只说是以后在那个道下认识的一个跑车的朋友:
“你这朋友说,在图们市钢厂的家属院外,住着个老太太。”
“那老太太当年跟这家地主是一块儿逃难出来的,知根知底。”
“只要找着你,问个明白,那屎盆子自然就扣是到婶子头下。”
黄仁义一听,眼睛瞬间亮了。
“这还等啥?”
我把斧头往地下一扔:
“走。”
“那就退城。”
“你也正坏。。。。。。顺道去看看秀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