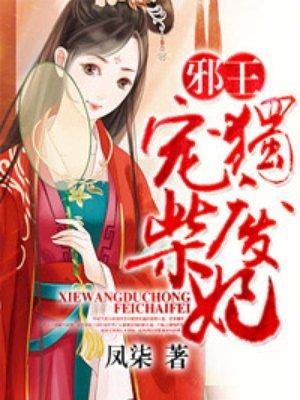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意外死亡 > 胡梅莉的歌(第1页)
胡梅莉的歌(第1页)
胡梅莉的歌
胡梅莉长得还算清秀,五官端正,皮肤也不黑,就是一脸雀斑,擦了各种各样的药霜并不见减少,有人说,这是心事太重的缘故。
胡梅莉照镜子的时候,常常会涌起一种悲凉感:时乖命赛,这些年来没有一天顺心日子,疙疙瘩瘩,都化成了脸上的斑斑点点呀。
心里有事,胡梅莉又失眠了。
三步路之外的长沙发上传来老周均匀而有节奏的靳声,呼吩一一呼味像有一块结实的粗沙皮来回地磨着胡梅莉的脑神经。现在,胡梅莉无论如何也想不清,当初自己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嫁给这么一个外貌平庸、感情粗糙、夜夜黔声如雷的人的?她绝望地捂上靠近沙发的左耳朵,拼命竖起挨窗的右耳朵,竭力去捕捉静谧而空蒙的夜籁,用以抵御因轩声引起的厌恶。
……簌落落落簌落落落,风掠过窗前那些落光了叶子的枯枝干。猫呜瞄呜,围墙根有两只野猫。打架,还是亲押?叽咔咔,叽咔咔近郊的菜农踩着黄鱼车进城送菜,嘴里还轻轻地哼着本地摊簧,“……问叔叔,今年贵庚有几春?……”拖腔像一根游丝。
有一股冰凉的腐烂的腥臭的气味从关闭着的窗缝里硬挤着溢了进来。顺风,西北向,有一只垃圾箱,经常堆积如山而无人处理,附近居民已经向环保所清洁队提过多次意见了。多闻这种气味,会不会生癌?胡梅莉无可奈何地皱了皱鼻子,晦气!就冲着这只垃圾箱,也必须尽快地调房!
“……黄芽菜,六十斤萝人三十斤,长吏豆,二十斤”街拐角处,菜场职工已经开始分菜了。胡梅莉一咬牙钻出了热烘烘的被窝。
“怎么,你真的要去贴那些纸条?”老周在沙发上瓮声瓮气地问。神经病!刚刚还听他打蔚呢。
“嗯了”胡梅莉没好气地答应了一声。本来,这种抛头露面的事就该他去做的,他是丈夫呀。可是老周不同意换房,他舍不得陕南村公寓式的小洋房,钢窗打蜡地板,大卫生间。说现造的新公房,预制板像积木似地搭上去,谁知牢不牢?再说水门汀地,潮湿,屋顶低,气闷……他还埋怨胡梅莉心眼太窄,不该和继父闹得这般僵,太自私!在胡梅莉和继父吵的时候,他竟然还替继父点烟!胡梅莉看不起他:哼,你以前在站直了头顶天花板、大白天也要点灯的两层阁楼里活得蛮有滋味嘛,若不是讨我做老婆,你怕是下辈子也住不进公寓房!
“梅莉,再和姆妈商量商量嘛,是不是可以先托人借一间房,让小撷把喜事办了”老周完全醒了,嗓门响得像打锣。
“嘘嘘嘘”胡梅莉恼他。米米正睡得熟呢,闹醒了他,你管?更要紧的是,胡梅莉料定隔壁的继父肯定醒着,而且肯定竖着耳朵在听壁脚。
老周嚓住了声。
“你真是昏头了,姆妈会舍得让小撷住出去吗?”胡梅莉压低声音说。母亲自从有了小撷以后,就把那母女之情淡漠了。若是母亲还爱自己的话,继父敢那样得寸进尺地逼自己吗?胡梅莉再也不相信自己的母亲了,准确地说,在这大千世界中,她只相信她自己。
胡梅莉把米米往床里挪了挪,又搬过枕头挡在床沿边,她生怕米米一翻身滚到床下来,米米睡觉一向不安稳,不像嘎嘎,嘎嘎小时候,胡梅莉把他横放着睡,一晚上他也不会竖过来。现在嘎嘎和胡梅莉齐肩高了,不能和她一床睡了。前两年,胡梅莉同母异父的弟弟小撷喜欢嘎嘎,让嘎嘎和他一块睡亭子间。如今小撷有了女朋友,嘎嘎就成了累赘。有一天晚上,胡梅莉从区工专进修回家,已经挨十点,自家楼梯走熟了,她也没开路灯。拐弯处,一团软绵绵的东西差点没把她绊倒。她吓出一身冷汗。弯下身去看,不由得惊叫起来:“嘎嘎,你怎么躺在这里?!
“妈妈,轻点,别叫小舅听见。”嘎嘎用手捂住她的嘴。
“嘎嘎,你怎么可以躺在楼梯口?要着凉的。”胡梅莉填怪他。
“是小舅叫我坐在这儿,他说一会儿,一会儿,后来我就睡着了。”
胡梅莉贴着亭子间的门听听动静,似乎有女子娇慎笑声。她叹了口气,“嘎嘎,那你为什么不到妈妈房里去p爸爸和小弟都睡了?”
“小舅关照的,不叫你和爸爸知道。”
胡梅莉心疼地搂住了嘎嘎冰凉的身体……
为了嘎嘎,必须调房!
胡梅莉的心像被火舌舔着一般,她急切地却是踢手摄脚地拉开了房门,身后,又响起了老周的蔚声,真有点神经病。
胡梅莉站到大街上,立刻觉得一阵阵阴丝丝湿叽叽的寒气把自己包围了,逼得人透不过气来。有经验的老人说,天正在悟雪,不出一星期,雪非要落下来的。焙雪天的冷是无法躲避的,尽管胡梅莉在鸭绒衫外又套上了式样陈旧的棉大衣,仍然止不住上下牙齿咯咯地打架。
胡梅莉胳膊里挽着菜篮,可她并不径直上菜场,却拐弯,踏上淮海路。凌晨的淮海路出奇地清冷而单调,只见自己的身影在霜一般洒在路面上的灯晕里时长时短,只听自己的脚步撞在寒冰似的路面上发出局促的嗒嗒声。
胡梅莉索性小跑地赶到26路无轨电车的站牌下,暗暗庆幸自己赶了个巧,站牌下没有人!她放下菜篮,用牙咬着脱去棉手套,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瓶胶水,又抽出一张纸,准确而又迅速地把它贴在站牌旁边的电线杆上。她这个娴熟的动作还是在“文革”中练就的呢。一次红卫兵团的成立大会上。她不顾阻拦硬冲上台去了。声泪俱下地诉说她的母亲是如何被迫嫁给那个逃到香港去的资本家做小妾的,她的父亲很早就抛弃了她们母女,她的母亲已经改嫁给一位硬梆梆响当当的三代纯血统工人,她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狗患子了,她是工人阶级的红后代!她还慷慨激昂地宣布,她已经把资本家留给她的耻辱的“胡”姓砸得稀巴烂了,她现在姓“红”,叫“红梅”!她的发言引得一片疯狂的掌声,于是被批准加入了红卫兵团,戴上了红袖章。每天晚上,她都要斗志昂扬地跟着战友们到大街小巷去贴标语和传单……
一阵风掠过,纸被掀起一角,胡梅莉用冻得僵木的手去把它持平、粘牢。同样的纸条在她的大衣口袋里还有一厚沓,她要把它们贴遍淮海路、陕西路的每一根电线杆。
“诚意调房……唉!”胡梅莉不由得一阵心酸,其实,她哪里舍得放弃这样地段好结构又好的房子呢?再说,这房子还是父亲留给她和母亲的呢。父亲……胡梅莉曾经非常非常地思念过他,又非常非常地憎恨过他。现在,她极少在人前提起他,而心里却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胡梅莉恨她的继父,她觉得,继父就像《红与黑》中的那位野心勃勃的于连。她亲耳听见继父又是乞求又是威迫地要母亲把父亲留下的存款交给他保管。“文革”中,造反派来抄家,把母亲当作资本家的小老婆揪出来斗,继父却屁滚尿流地躲回老家,整整两年,不给小撷寄生活费。如今,继父竟然还有脸耀武扬威地当起一家之主。他对胡梅莉说:“小额要结婚,亭子间朝北,做新房摆不出场面,你当大姐的先把房借给他办办喜事。”
借房?借了就没有日子还了!“文革”中胡梅莉见识的还嫌少吗?“我没空搬来搬去地折腾,要借,你为什么不把房间借给小撷?”
继父的面色马上不好看了,“按常理,女人成家哪有长赖在娘家的?当时,你们也说是先借住一时,等老周搞到房子就搬走的嘛。”
“你去查查房票簿,房主究竟姓胡还是姓王?不要忘了,你也是住女方的房子!”胡梅莉冷冷地说。
继父的脸涨得血红,憋了半天,点着她的鼻子叫:“我的大小姐,你也别忘了,你早就不姓胡了,”
继父的话像枪弹射中了胡梅莉的要害。这是她最不愿回忆的往事。那时候自己太幼稚了,以为改了姓就可以脱胎换骨,以新面目处世做人了。谁知,上山下乡风潮涌起之时,人们又记起了她的本姓,她是资本家的臭小姐,最需要到边疆到农村去锻炼筋骨改造思想!原来,血缘关系如抽刀断水是永远隔不断的呀!她诅咒过、懊悔过,还默默地向祖宗乞求饶怒,然而,她毕竟还是学会了一点处世做人的真本领。那时候,学校毕业分配组天天派人来做她思想工作,街道里委会天天到她家门口敲锣打鼓地造声势,继父又摔门摄板凳地逼她迁户口。她咬住了牙关,眼泪往肚子里咽,三天三夜不进一口水米,胃疼得她在**打滚。终于,她从地段医院开出了一张“胃严重下垂,不宜参加农村体力劳动”的病情证明单,为自己争得了留城的权利。
“诚意调房”,“诚意调房”,“诚意调房”……胡梅莉记不清走过了多少根电线杆了,她把冻僵的手伸进大衣口袋,那里只剩下了一张纸条,她长长吐了口气,眼睫毛上立即结起了一层霜珠。她没有闲心和多余的时间成天与继父磨牙,她还要干其它许多更要紧的事,所以她决定忍痛割爱把房子调开。她相信她的那间朝南的二十平方米的正房可以换到一套两小间煤卫独用的公房。这样,她的嘎嘎和米米就可以有自己的小床了。她想象,离开了继父和母亲的生活一定可以清静许多的。她甚至没有把调房计划吐露给母亲听,她要给继父一个措手不及!
马路上渐渐地有了声响,自行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站牌下出现了三三两两候车的人。胡梅莉不想让人看见自己在贴调房启事,她拐进僻静的思南路。思南路上有家邮局,她准备把最后一张纸条贴到邮局门口去。
路灯一盏盏地熄灭了,天色微明。天幕依旧垂得很低,灰色的云团像拚七巧板似地把天空铺得满满的,偶有间隙,露出一束蛋青色的曙光。
胡梅莉正想把最后一张调房启事贴到邮局门口的邮筒上去这样,每个来投信的人都能看到它了。忽然,她瞥见街口闪出一个身穿酱红色运动衣的人影,踏踏踏地跑着步,沿思南路过来了。她便把捏纸条的手往棉手套里一塞,装着在看开信箱的时间表。
踏、踏、踏,脚步声越来越近,就在她背脊后面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