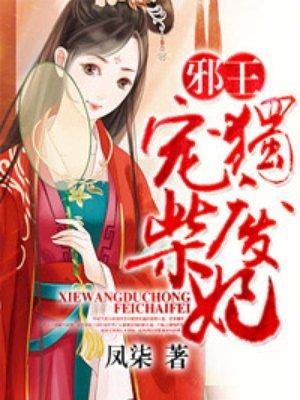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寻宝人的故事 > 第11章 卡斯蒂利亚葡萄醇香酒(第2页)
第11章 卡斯蒂利亚葡萄醇香酒(第2页)
爱丽斯听见了,从恍惚中清醒过来。她突然说话,说得非常快——快得我知道她事先就想好了要说什么的。她从广告里了解到许多情况。
她说:“我请你注意我这里的雪利酒样品。这种酒叫做卡斯蒂利亚什么的,以香味而论它的价格是无与伦比的。”
屠夫说:“嗯——我不买!”
爱丽斯继续说:“尝一点好吗?”
“非常感谢,一定尝一点,小姐。”屠夫说。
爱丽斯倒一些出来。
屠夫尝了一点点。他舔着嘴唇,我们想他要说味道多么好。但他没有,而是把酒杯放下,几乎所有酒都剩在杯里(后来为了不浪费我们把酒倒了回去)。他说:“请原谅,小姐,不就是有一点甜味吗?——我的意思是雪利酒?”
“真正的酒并不甜。”爱丽斯说。“如果你订购一打就完全不同了——我们最喜欢加糖。我希望你能订购一些。”屠夫问为什么。
爱丽斯一时没有说话,后来才说道:
“我不在乎告诉你:你自己在做生意,对吧?我们打算让别人买这种酒,因为只要能让任何人买酒,我们每卖出一打就可赚两先令。这是一件让人满意的事。”
“有一定比例的利润,对,我知道。”屠夫说,眼睛看着地毯上的洞。
“你知道有许多理由,”爱丽斯继续说,“使我们想尽快发财。”
“完全是这样,”屠夫说,他看着一处地方,那里的纸正从墙上掉下来。
“这似乎是一个好办法。”爱丽斯继续说。“我们花两先令买了样品和说明,说是利用业余时间每周轻易就赚两英磅。”
“当然我希望你能,小姐。”屠夫说。爱丽斯又问他愿意买一些吗?
“我是很喜欢雪利酒的。”他说,爱丽斯请他再喝一点。
“不用了,谢谢你,小姐。”他说。“这是我很喜欢的酒,但它并不合我的口味,一点都不。不过我有一位叔叔要喝这酒。也许我可以给他定购半打作为圣诞节礼物?嗯,小姐,不管怎样,先给1先令的代办费。”他掏出一把钱,把1先令给了她。
“可我原以为人们要先付钱买这酒。”爱丽斯说。
屠夫说他们并不是要买半打。然后他说,他想不用再等爱丽斯的父亲了——爱丽斯愿意请父亲给他写信吗?
爱丽斯又请他喝雪利酒,他说着有关“一点也不喝了!”的话——她让他走了,然后带着1先令向我们走来,说“怎么会这样?”
我们说:“唉!”
整个晚上我们都谈论自己开始赚到的钱。
第二天没有人来了,但又过了一天后一位女士前来摹捐,要替已故海员们的孩子们修一所孤儿院。我们看见她,我随爱
丽斯进了屋。我们向她解释我们只有1先令,想用它换点别的什么,这时爱丽斯突然说:“来点酒好吗?”
女士说:“非常感谢。”她看起来很惊奇。她并不是一位年青女士,披着一件带珠子的披风,有些珠子已经掉了——棕色的镶边显露出来。她把印着已故海员情况的材料放在一只海豹毛皮包里,海豹毛皮已经褪掉,只留下光光的皮子。
我们用餐具柜里的专用酒杯给她倒了一汤匙酒,因为她是一位女士。她尝了酒,便慌慌忙忙地站起来,抖了抖衣服,迅速把包关上,说:“你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孩子!这样搞恶作剧是什么意思?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我要写信告诉你们的妈妈。你这个该死的小女孩!——你们差点毒死我。不过你们的妈妈……”
这是爱丽斯说:“我非常抱歉;屠夫喜欢这种酒,只是他说是甜的。请不要写信给我妈妈,她收到了信父亲会很不高兴!”爱丽斯几乎要哭了。
“你是什么意思,你这个傻孩子?”女士说,看起来既很乐观又很感兴趣。“为什么你父亲不愿意你母亲收到信——嗯?”
爱丽斯说:“噢,你——!”她哭了起来,跑出屋子。
我说:“我们母亲已经死了,你现在请离开了好吗?”
女士看了我一会儿,显得十分异样,说:“我非常抱歉。我不知道。酒的事别在意。我敢说你的小妹本意是好的。”她就像屠夫一样把屋子打量了一番。然后她又说“我不知道——我非常抱歉……”
于是我说:“没关系,”同她握了手,让她走了。当然,她说了那些话以后我们不可能再让她买酒了。我想她并不是某种坏人。我很喜欢一个应该道歉时就道歉的人——特别是一个成人。他们很少这样做。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此考虑那么多。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爱丽斯和我都不高兴。我走回餐室时,看到它与母亲在时多么不一样,我们也不一样,父亲也不一样,一切都变了。我很高兴没有每天去想这事。
我去找到爱丽斯,把那位女士说的话告诉了她,等她不再哭时我们把酒瓶移开了,而且说我们不再卖给来的人。我们没有告诉其他人——只说那位女士什么都没买——我们去了希思,有一些士兵经过,那儿正在演“潘趣和朱迪滑稽戏[26],我们回来时心情好些了。我们放在屋里的那瓶酒已积满灰尘,也许有很多年代的灰尘都厚厚地积在了上面;我们不在家都时,只有一个牧师来访。他不是我们自己的牧师——布里斯托先生才是我们的牧师,我们都喜欢他,不愿意把雪利酒卖给自己喜欢的人,利用我们的业余时间从他们身上每周赚两英镑。来的是另一位牧师,他走迷了路,问伊莱扎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是否不喜欢上他那所小小的主日学校。礼拜天下午我们总是和父亲一起度过。但由于他把自己住宅的名字留给了伊莱扎,要她告诉我们去上学,我们便认为应该去拜访他,把礼拜天下午的情况向他作解释,心想也可带上雪利酒去。
“除非你们都去我才去,”爱丽斯说,“并且我不想谈卖酒的事。”
多拉说她想我们最好不要去,但我们说“废话!”最后她还是随我们一起去了,我很高兴她这样做。
奥斯瓦尔德说如果其他人同意,卖酒的事就让他谈。他从印刷品上学会了该怎么说。
星期6下午我们很早就去了牧师住宅,按响门铃。这是一栋红色的新房子,园里没有树,只有很黄的泥土和砾石。一切都很整洁干燥。就在我们按门铃前,我们听到里面有人在叫:“简!简!”我们想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是简。听见喊叫的声音,我们替叫的人感到难过。
一个穿着整洁的黑衣服、围着白围裙的仆人打开了门;透过门上不同颜色的玻璃,我们看见她走过大厅时一边设法解开围裙带子。她的脸红红的,我想她就是简。我们问是否能见到马洛先生,仆人说马洛先生刚才还忙于讲道,不过她会去看看。
但奥斯瓦尔德说:“没有关系。他要我们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