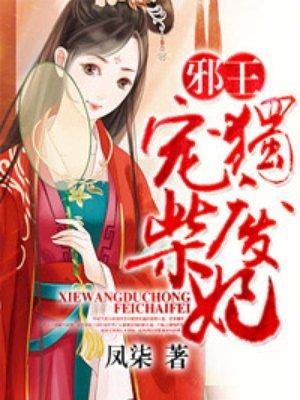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夏日之旅3·谁能规定我们的一生 > 十九 一棵不会结果子的百香果带来的启示(第2页)
十九 一棵不会结果子的百香果带来的启示(第2页)
“我给你们寄的手绣丝巾怎么样,那是新开发出来的纳米布料。现在外边讲手绣大多数是骗人的,能是手握绣这种半人工的就比机绣要难得一百倍了。”林婆婆又说。
“老沈选了那条蝶恋花的,不过她从不用,说是好东西不舍得。”
“是什么好东西,用坏了我那儿多得是。”林婆婆讪讪的。
出殡了就往山上走。
只有最亲的人会陪着一起上山,小林爷爷、儿子媳妇孙子女儿女婿乌泱泱一群人簇拥着骨灰盒走山路。
骨灰盒放在寺庙里,一个个的小格子承载着一个人的一生和灵魂。
“现在都不准土葬了,我们这儿山这么多……”林婆婆的语气里有些遗憾。
她和外婆跟在家人后面,一起送别老姐妹一程。
要到寺庙去须得渡河,河边有摆渡的人,身材魁梧,一支桨儿划得飞快。
人太多了,林婆婆和外婆就没再跟着。
她们站在河边,目送着沈婆婆远去,从此就天人两隔,再也听不到那爽利的大嗓门,见不到那笑皱了的脸,听不到敲窗声。
死亡带走的不仅仅是肉体,还有无数的回忆。
昨日不可再来,同样的,明日也只有一次。
外婆一直都没有哭,直到这时候眼泪才落下来。
林婆婆的眼眶也红了,她试探着伸出手,揽住了外婆的肩。
这个亲密的动作终于打破了隔阂和一些难以跨越的沟壑。
老姐妹俩相携着胳膊往回走。
林婆婆多住了几天,最后一天早早和外婆去了寺庙。
大雾弥漫,山林被乳白色的重纱罩住了。
朦胧中听见衣物擦过枝叶的窸窣声。
喘气声——这来自林婆婆。
“老了,一爬山路腿就乏了力。”
林婆婆和外婆走一段路歇一阵。
外婆背了个背篓,篓里有院子里刚剪下的花,不拘一定要**,大大捧的各式花拢在一起。
篓底还有一瓶荔枝酒。
荔枝酒是去年沈婆婆和外婆一起酿的。
南风镇近山有荔枝园,桂味荔枝核小肉厚味浓,单剥来吃也是上品,用来酿酒再好不过了。
酿荔枝酒要剥掉皮,晨露中的荔枝还是湿的,要等到十点多的时候,太阳没那么晒,把荔枝摘下来,剥皮,不用去核,一层荔枝一层冰糖地铺在黑瓦窄口罐里,再倒入高粱酒。
酒的度数不能低,低了要馊,也酿不出味道来。
外婆盖上盖子,沈婆婆再盖一层红棉布,用绳子把布连盖子紧紧地匝起来打结,放到阴凉通风的储藏室。
三个月后,性子急的就可以拿出来喝了。
“春来收到蜂蜜,夏季收到荔枝酒,秋天收到赤小豆和黑糯米,冬冷收到腌冬菜,瓶瓶罐罐的堆满了储藏室……”林婆婆轻声地说,“你和老沈过得有滋有味,不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