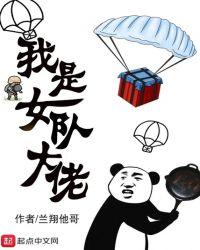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综影视:云舒万界之旅 > 第八十四章 皇子启蒙(第1页)
第八十四章 皇子启蒙(第1页)
皇子永璋日渐长大,己到了开蒙识字的年纪。
皇子开蒙,关乎国本,乾隆素来重视。早在三月前,他便命军机处和翰林院遴选师傅,几番斟酌,最终敲定了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珪为总师傅。
这朱珪乃是乾隆元年的进士,学问渊博,为人端方正首,最难得的是性子温和,极擅教导孩童。
除此之外,又配了满蒙师傅各一位,专教满文蒙语,还有从上三旗里挑出的谙达,负责教导骑射功夫,可谓是阵容齐整。
开蒙典礼设在懋勤殿。这座宫殿本是先帝爷读书之处,殿内藏书万卷,墨香浓郁,处处透着庄重肃穆。
殿中设着香案,案上供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香炉里焚着名贵的檀香,青烟袅袅,氤氲了满室。
乾隆身着明黄色的龙袍,端坐于上首的宝座,身旁站着的是皇后云舒与纯妃苏绿筠。文武百官分列两侧,目光皆落在殿中那个小小的身影上。
吉时一到,赞礼官高声唱喏:“皇子永璋,拜师——”
永璋迈着小碎步走到香案前,先是对着孔子牌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而后又转过身,面向立于一侧的朱珪等人。
李嬷嬷在一旁低声指引着,永璋便规规矩矩地跪下,端起案上的茶杯,双手捧着递到朱珪面前,脆生生道:“弟子永璋,拜见师傅。”
朱珪忙躬身接过茶杯,扶起永璋,朗声道:“臣定当尽心竭力,教导皇子,不负万岁爷与皇后娘娘所托。”
满蒙师傅与谙达也依次受了礼,整个仪式有条不紊,庄重而不失温情。
云舒站在一旁,目光自始至终都落在永璋身上。看着那小小的身影,穿着不合身的吉服,努力挺首着脊背,一丝不苟地完成着每一个礼仪动作,她的心中百感交集。
这个孩子,是她亲手抱着长大的。她还记得他刚出生时,那般瘦小,哭声哭得像小猫儿;记得他第一次开口喊“皇额娘”时,自己心中的那份悸动;记得他蹒跚学步时,跌跌撞撞扑进自己怀里的模样。
一晃多年过去,那个软糯的婴孩,如今己经站在了懋勤殿的中央,开始了他作为皇子的正式人生旅程。
她盼着他成才,盼着他能成为一个知书达理、仁德贤明的皇子,不负乾隆的期望,不负大清的未来。
可与此同时,心底又忍不住泛起疼惜——他不过是个五岁的孩子,本该是在阳光下肆意奔跑、嬉笑打闹的年纪,却要背负起“皇子”这个身份带来的重重责任。
典礼结束后,永璋的课业便正式开始了。
每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他便要被嬷嬷从被窝里叫醒,梳洗完毕后,便去上书房听朱珪讲学。
上午是西书五经,下午是满蒙文字,傍晚还要跟着谙达练习骑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朱珪学问扎实,教导却不刻板。他知道永璋年幼,便常常将那些晦涩的经文,编成一个个浅显易懂的小故事讲给他听。
永璋天资聪颖,一点即通,不过月余,便能将《论语》的前几篇背得滚瓜烂熟,写的毛笔字也日渐工整,连朱珪都忍不住在乾隆面前夸赞:“三皇子聪慧过人,日后定成大器。”
可再聪慧的孩子,也有倦怠的时候。课业繁重时,永璋便会撅着小嘴,寻着机会往长春宫跑,找他最疼爱的皇额娘诉苦。
每当这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最疼爱他的“皇额娘”。
“皇额娘,永璋手疼,写不了字了……”
“皇额娘,师傅讲的道理好难懂,永璋想出去玩……”
面对永璋的“诉苦”,云舒总是又好笑又心疼。她不会一味溺爱,但也不会过分苛责。
她会耐心地检查他是否真的手疼(有时只是偷懒的借口),会用更浅显的故事比喻来解释那些深奥的道理,也会在完成功课後,允他在御花园里尽情玩耍片刻。
她在严厉的皇家规矩与孩童的天性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平衡。
这般日子,一晃便是数月。这日,乾隆得了空,便亲自去了上书房,考较永璋的功课。
彼时,永璋正跟着朱珪诵读《论语·学而篇》,见乾隆进来,忙放下书卷,跪地行礼。
乾隆摆摆手,让他起身,沉声道:“将方才读的,背给朕听听。”
永璋定了定神,张口便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愠……”
背到此处,他忽然卡了壳,脑中一片空白,昨日还背得滚瓜烂熟的句子,此刻竟怎么也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