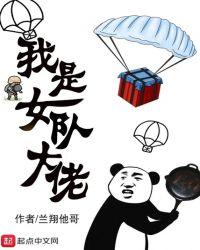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梅子金黄杏子肥 > 第133章 咱们也是来求财的不是来结梁子的(第1页)
第133章 咱们也是来求财的不是来结梁子的(第1页)
那个叫“彪哥”的男人一开口,周围原本嘈杂的电子市场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几个原本蹲在地上挑挑拣拣的散客,一看这架势,把手里的东西一扔,缩着脖子就溜了。
在这片泥泞的上步工业区,“彪哥”这俩字,比派出所的红戳子还好使。
彪哥穿着件领口大开的花衬衫,胸口那一撮黑毛上挂着个手指粗的金链子,随着他的晃动一荡一荡的,晃得人眼晕。他嘴里叼着半截牙签,那双三角眼微微眯着,透着股被南方的湿热腌入味的油滑和狠戾。
他身后那几个马仔,手里都拎着从钢管厂顺出来的镀锌管,有的还在掌心里有一搭没无一搭地敲着,“啪、啪”作响,像是某种倒计时的催命符。
“靓女,怎么不说话了?”彪哥往前晃了两步,脚上的鳄鱼皮鞋踩在烂泥里,发出“吧唧”一声腻响。他伸手在那堆沾满黄泥的主板上拍了拍,“刚才不是挺能侃价的吗?这堆废塑料,一块钱一斤?你当我是收破烂的?”
英子心里那根弦绷得死紧。她太清楚这种地头蛇的套路了——这堆东西在他眼里原本就是垃圾,但只要看你想要,那垃圾立马就能变成古董价。
“老板,做生意讲究个先来后到。”英子强压着心跳,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带着一股子北方人的硬气,“价钱我们都谈好了,您这半路杀出来,不太合规矩吧?”
“规矩?”彪哥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仰头大笑,露出两颗镶金的大门牙,“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我王大彪的话就是规矩!这堆货,我现在看上了,不想卖了,怎么着?”
其实他根本不知道这堆破板子有啥用,但他看人准。刚才他在旁边瞧了半天,这小姑娘虽然嘴上嫌弃,但那眼神可是骗不了人的——那是一种饿狼看见肉的眼神。既是肉,那就得狠狠咬下一口油来。
“两千块。”彪哥伸出两根手指,狮子大开口,“一口价,这堆垃圾你拉走。少一个子儿,你们俩今天就留在这儿给我数泥点子。”
两千块!
那个收破烂的老板吓得脸都白了,这堆东西按废铁卖顶多值个五十块。
英子攥紧了拳头。两千块她拿得出来,但绝不能拿。这年头露财就是找死,今天给了两千,明天这帮人就能追到旅馆去抢两万。
就在这时,一首站在英子身前没说话的陆泽坤动了。
他没掏钱,也没求饶,而是慢慢地、旁若无人地从兜里掏出了一盒皱巴巴的“大前门”。
“二哥……”英子下意识地拉了一下他的衣角。
陆泽坤没回头,只是用身体把她挡得严严实实。他用左手大拇指熟练地弹出一根烟,叼在嘴里,然后又摸出一盒火柴。
这动作太稳了,稳得让对面的彪哥都愣了一下。
在这个剑拔弩张的时候,这残废居然还有心思抽烟?
陆泽坤左手捏着火柴盒,用大拇指指甲盖抵住火柴头,“呲”地一声,单手划燃了火柴。橘红色的火苗在潮湿闷热的空气里跳动了一下,照亮了他那张布满胡茬、冷硬如铁的脸。
他歪着头,深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模糊了他的眉眼。
隔着烟雾,他那双眼睛像两把刚磨过的杀猪刀,死死地钉在彪哥脸上。那种眼神,不是装出来的凶,那是真的见过血、在死人堆里爬过之后才有的漠然。
“怎么个意思?想黑吃黑?”陆泽坤的声音沙哑低沉,像是嗓子里含着一把沙砾。
彪哥被这眼神盯得后背一凉,本能地往后退了半步,随即又觉得丢了面子,恼羞成怒地指着陆泽坤那只戴着黑手套的右手:“死瘸子!这里轮得到你说话?信不信老子把你那只废手给剁下来喂狗?”
空气瞬间凝固。
几个马仔提着钢管就要往上冲。
陆泽坤嘴角勾起一抹让人看不懂的冷笑。他没躲,反而往前跨了一步,那只一首垂在身侧、毫无生气的右手,缓缓地抬了起来,落在了旁边一张用来称重的铁桌子上。
桌子上,正好放着一个刚喝完的铁皮罐头盒——那种装午餐肉的厚铁皮盒子,硬得很,普通人用脚踩都得费点劲。
“剁手?”陆泽坤轻蔑地哼了一声,嘴里的烟灰都没抖一下,“那得看你的刀够不够快。”
话音刚落,他那只戴着厚厚黑色牛皮手套的右手,突然按在了那个铁皮罐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