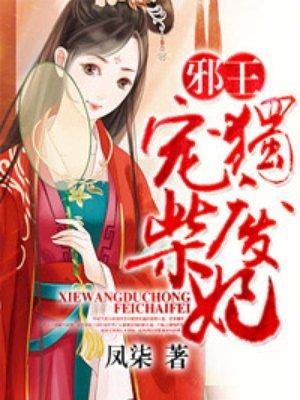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雾都孤儿 > 第五十一章 本章解开了不止一个谜团还叙述了一门只字未提婚姻财产协议和零花钱1的亲事(第2页)
第五十一章 本章解开了不止一个谜团还叙述了一门只字未提婚姻财产协议和零花钱1的亲事(第2页)
“闭嘴,蠢货。”邦布尔太太嘟哝道。
“这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邦布尔太太?”救济院院长反驳道,“我受教区委托把他抚养大,现在看到他就坐在最和蔼可亲的女士们、先生们中间,我能不高兴吗?我一直很爱这孩子,就好像他是我的——我的——我的亲爷爷。”邦布尔先生结结巴巴,好不容易才找出一个恰当的比方,“奥利弗少爷,我亲爱的小少爷,你还记得那位穿白背心的老绅士吗?啊!上礼拜他升天了,福气不浅啊。棺材是栎木的,还有镀金的把手呢,奥利弗。”
“行了,先生,”格里姆维格先生不无尖刻地说,“克制一下你的感情吧。”
“我会努力克制的,先生。”邦布尔先生应道,“您好吗,先生?但愿您身体健康。”
他是在向布朗洛先生问好,后者已经走到离这对可敬夫妇很近的地方。布朗洛先生指着蒙克斯问道:“你们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邦布尔太太斩钉截铁地答道。
“或许你也不认识?”布朗洛先生又问她的丈夫。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他。”邦布尔先生说。
“或许也没卖过什么东西给他?”
“没有。”邦布尔太太答道。
“或许你们也从未有过一只小金盒和一枚戒指?”布朗洛先生说。
“当然没有,”女舍监答道,“为什么要带我们来这里回答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布朗洛先生再次向格里姆维格先生点点头,后者再次一瘸一拐地走出房间,动作异常敏捷。但这回他带进来的不是一对胖夫妇,而是两个患过中风的老妇人,她们哆哆嗦嗦、踉踉跄跄地走进房间。
“老萨莉死的那晚,你把门关上了。”走在前面的老婆子举起一只皱缩的手,“可你关不住声音,也堵不住门缝。”
“对,对,”另一个老婆子说,往四周打量了一下,颤动着没有牙齿的嘴巴,“说得对。”
“我们听见她努力要把自己干过的事告诉你,还看到你从她手里接过一张纸。第二天,我们还看到你进了当铺。”第一个老婆子说。
“没错,”另一个老婆子补充道,“那是‘一个小金盒和一枚金戒指’,我们打听清楚了,还看见东西交到了你手里。我们当时就在边上。噢!就在边上。”
“我们知道的还不止这些哩。”第一个老婆子接着说,“很久以前,我们常听老萨莉讲,那位年轻的母亲告诉过老萨莉,她觉得自己肯定不行了,便要去孩子父亲的坟前死在那里,谁料竟然半路病倒了。”
“你们想见见当铺老板本人吗?”格里姆维格先生问,做出要往门外走的样子。
“不必了,”女舍监答道,“既然他——”她指着蒙克斯,“是个胆小鬼,把什么都招了——我看他全说了——既然你们已经调查了所有的老婆子,找到了两个合适的证人,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我确实把那两件东西卖了,它们已经落到了你们永远找不回来的地方。那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布朗洛先生答道,“只是,我们可以留心一件事,那就是:你们两位都不能再担任需要承担责任的职务了。你们可以走了。”
“我希望,”格里姆维格先生带着两个老婆子出去以后,邦布尔先生环顾四周,可怜巴巴地说,“我希望,这件不幸的小事不会害我被革去教区的职务吧?”
“革职是肯定的,”布朗洛先生答道,“你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要知道,这样的结果对你们来说算是很幸运的了。”
“这都是邦布尔太太的主意。她非要那么干。”邦布尔辩解道,但说话前先打量了周围一圈,确定他的夫人已经离开了房间。
“这借口不顶用。”布朗洛先生应道,“销毁这些小饰品的时候你是在场的,而且从法律的角度看,你们两人当中,你的罪更重,因为法律认为你妻子是在你的支配下行动的。”
“如果法律如此认为,”邦布尔先生说,双手使劲揉搓着帽子,“那法律就是头蠢驴——是个白痴。如果法律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那法律就是个老光棍儿。但愿法律也落得最可怕的下场,就是通过切身体验来看看,丈夫能不能支配妻子——这非得切身体验不可。”
将“切身体验”四个字强调一遍后,邦布尔先生把帽子死死扣在头上,两手插进口袋,跟着他的贤内助下楼了。
“小姐,”布朗洛先生转向罗丝说,“把手给我。不要发抖。你不用害怕,听我把剩下几句非说不可的话说完。”
“如果你要说的话跟我有关,”罗丝说,“我知道这不大可能,但如果确实与我有关,请换个时间再告诉我吧。我现在既没有气力,也没有精神。”
“不,”老绅士挽起她的胳膊应道,“我敢肯定,你是非常坚强的,扛得住这点事。你认识这位小姐吗,先生?”
“认识。”蒙克斯答道。
“我从未见过你。”罗丝有气无力地说。
“我可是见过你好多次。”蒙克斯应道。
“苦命的阿格尼丝,她父亲有两个女儿,”布朗洛先生说,“另一个女儿——当时她还很小——她命运如何呢?”
“她父亲客死异乡,”蒙克斯讲道,“还改换了姓名,又没留下什么信件、本子或是字条,可以给亲戚朋友提供一丁点追踪的线索,于是,那个小女孩被一户穷苦的农民领走,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了。”
“说下去,”布朗洛先生一边说,一边示意梅利太太过来,“说下去!”
“那户人家后来搬到别处去了,你想找也找不到。”蒙克斯说,“不过,友情无能为力的事情,仇恨往往能强行办到。我母亲费尽心思搜寻了一年,终于找到了那个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