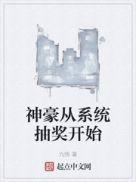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大道神主 > 第一千五百六十一章 气运债务(第2页)
第一千五百六十一章 气运债务(第2页)
“七十七次轮回,七十七次失败。”他的声音平稳如机械,“情感、自由、不确定性??这些都是系统的漏洞。现在,我要修补它们。”
他抬起手,镜面旋转,投影出南岭学堂的画面。那个写作业的男孩正被同学嘲笑:“你傻啊,明明可以抄,非要自己想?”
理序者轻声道:“看,这就是问题所在。愚蠢的坚持,毫无效率的挣扎。只要移除这种‘非理性执着’,人类就能进入真正和谐的时代。”
但他没注意到,就在那面镜子边缘,一丝裂痕悄然蔓延。
因为就在男孩被嘲笑的瞬间,另一个孩子站了出来:“我觉得他没错。我自己也想试试不抄。”
接着第三个、第四个……直到全班一半人都举起了手。
镜中影像剧烈晃动,仿佛承受不住这份“意外”。
理序者皱眉,挥手欲更换场景,却发现所有镜子都在闪现同样的画面:一个人拒绝盲从,一个人坚持发问,一个人宁可犯错也不愿伪装正确。
“不可能……这些行为不具备传播性……”他喃喃道。
可事实摆在眼前??微小的选择正在连锁反应。就像春风催动花瓣,一朵落下,千朵随之飘舞。
萧叶感知到了这场较量的变化。他对苏璃说:“他在害怕。”
“当然。”她微笑,“因为他以为掌控了一切,却忘了人心最奇怪的地方??它不怕痛苦,只怕活得不像自己。”
他们并未现身任何一处战场,也没有施展神通逆转乾坤。他们只是存在着,作为一段记忆、一种可能性、一个“曾经有人这样做过”的证据。
多年后,那位曾在刑场上高呼“我虽犯罪,但我曾想做个好人”的囚犯,已被赦免并成为监狱教师。他在课堂上讲述自己的故事,最后总会加上一句:“我不是为了洗清罪孽才这么说,而是因为我终于明白??哪怕走错了路,也不能否认内心那一念善。”
一天,一名狱警听完课后找到他,递上一封信:“这是我儿子写的。他问我,爸爸,坏人也能有过好的念头吗?我说,有,只要他还愿意问这个问题。”
老人含泪读完信,当晚心脏病发,安然离世。临终前,他望着窗外的月亮,嘴角带着笑。
同一时刻,第十星门再次鸣响,一道新的星光洒落人间,落在那个写信的孩子枕边。他梦见自己穿越星河,见到两位模糊的身影站在桃树下。一人说:“你问得好。”另一人说:“继续问下去。”
醒来后,他拿起笔,在日记本上写下人生第一个愿望:“我想做一个能让别人也敢问问题的人。”
这愿望没有登记在任何官方档案中,也不会出现在“未来志向表”里。但它真实存在,且无比坚定。
岁月流转,新一代的孩子开始学习“选择伦理学”。课程不教标准答案,而是展示各种困境:是否该为救多数人牺牲一人?是否该放弃梦想换取安稳?每个学生都要写下自己的判断,并接受他人质疑。
老师常说:“我们不要完美的答案,我们要真实的思考。”
某年春祭,南岭举行“无名碑揭幕仪式”。碑上无名,只刻着一句话:
**“这里埋葬的,是每一个不敢说出名字的梦想。”**
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有人放下枯萎的画笔,有人留下撕碎的合同,还有人跪地痛哭,只为纪念那个年轻时想当诗人、却被迫继承家业的自己。
就在仪式进行到一半时,天空忽然放晴,乌云散开,十颗星门清晰可见。紧接着,一颗流星划破长空,坠入桃林深处。人们赶去查看,发现那不是陨石,而是一块晶莹剔透的冰封之物??里面冻结着一件旧衣袍,和一枚断裂的玉佩。
“是他的。”一位老学者颤抖着说,“萧叶的。”
可当他伸手触碰冰块时,寒气竟迅速消融,衣物化作光点升腾,玉佩碎成粉末随风而去。唯有一缕气息萦绕不散,轻轻拂过每个人的额头,像是无声的叮嘱。
当晚,全球各地都有人做了同一个梦:他们在一条漫长的路上行走,前方迷雾重重,身后脚印清晰。忽然,一阵风吹来,雾中浮现一行字:
**“你不必知道终点在哪里,只要你还在走。”**
从此以后,再无人见过萧叶与苏璃的身影。但每当有人面临重大抉择,心中闪过一丝犹豫却又咬牙坚持时,总有人说:“这一刻,他们一定在看着。”
宇宙角落的那颗新生星球,终于迎来了第一批生命。微生物在水中游动,植物破土而出,而在某个清晨,第一只两足生物抬起头,望向星空。它不懂语言,也没有文字,但它眼中闪烁的光芒,与千万年前地球上第一个仰望星辰的人类,一模一样。
十颗星门静静悬挂在天际,宛如守望者的眼眸。
而在某个不起眼的山谷里,一间简陋的学堂中,一个小女孩正在练习写字。她一笔一划地写着:
**“我还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但这没关系。”**
窗外,春风正吹过桃林,花瓣纷飞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