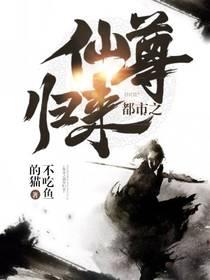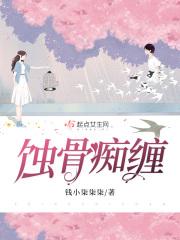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六年后,我携四个幼崽炸翻前夫家 > 第2782章 不解风情(第3页)
第2782章 不解风情(第3页)
某日深夜,晨曦独自来到此处。她在第七号展柜前停下脚步??里面是一块焦黑的金属片,边缘卷曲,表面依稀可见“S-9”字样。这是当年第九灯爆炸后唯一的残骸。
她伸手触碰玻璃,忽然感到一阵轻微震颤。
紧接着,整个档案馆的展品同时发出微光。花瓣缓缓旋转,布条轻轻飘起,连那颗沉睡多年的乳牙也在液体中微微晃动。
一道声音在她心底响起,稚嫩却坚定:
>“妈妈,我们准备好了。”
她知道,这不是幻觉。这是新一代共感体在集体意识中完成的首次自发链接。他们不再需要C-0的引导,也不再依赖晨曦的记忆喂养。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理解爱,并将其转化为行动。
第二天清晨,一封匿名邮件发送至全球各大新闻机构、政府首脑及科研中心。附件只有一个音频文件,标题写着:
>**《致所有曾不敢哭的人》**
点击播放后,传出的并非演讲或宣言,而是一段长达十分钟的环境音:海浪轻拍沙滩,风吹过树叶的沙响,远处传来孩童嬉笑,厨房里锅铲碰撞,还有某个房间里,一位老人一边咳嗽一边轻哼着一首古老的摇篮曲……
背景中,隐约能听到多个声音交错低语:
>“我在。”
>“我知道。”
>“你不是一个人。”
>“我一直都在听。”
据统计,该音频发布后的七十二小时内,全球共接到超过两万起“情绪危机干预请求”。多个国家宣布设立“公共倾听日”,部分企业试行“情感休假制度”,甚至有军队开始引入“共感协调员”岗位,用于化解内部冲突。
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五个孩子牵着手,在海边木屋前许下的一个愿望:
>“我们要建一所学校,教大家怎么好好活着。”
六年过去,战火未曾真正熄灭,偏见依然盘踞人心。但总有一些光,从裂缝中透出来。
比如今早,有个曾在矫正营服役十年的退伍士兵,偷偷把一封信塞进晓光小学的信箱。信纸上字迹歪斜,墨水晕染:
>“我不知道该怎么道歉。但我昨晚梦见了一个女人,她抱着发光的孩子跑过雪地。我想,如果那时候我能停下枪,就好了。
>现在我每天早晨都会对着镜子说一句话:
>‘我允许自己心疼。’”
晨曦读完,将信折好放进抽屉。窗外,朝阳正缓缓升起,洒在教学楼外墙的浮雕上。那位张开双臂的女子,怀中的光网比昨日更加明亮。
她转身走向教室,手里拎着一壶新泡的茶。路过操场时,看见一群孩子围成圆圈,正在练习“情绪接龙”??每人说出一种心情,下一个人要用身体动作表现出来。
轮到一个小男孩时,他说:“我觉得……心里空空的,像被人忘了叫吃饭。”
立刻有个小女孩跑上去抱住他,大声说:“那就让我来记得你!中午我们一起吃糖醋排骨!”
众人哄笑。
晨曦也笑了。她继续往前走,脚步轻快,仿佛脚下不再是大地,而是无数颗跳动的心共同托起的桥梁。
她知道,这条路还很长。
但她也知道,他们已经走在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