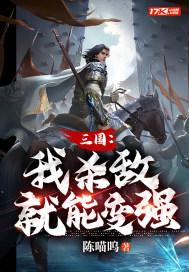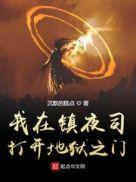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财富自由从毕业开始 > 第650章 动物世界(第3页)
第650章 动物世界(第3页)
清明节前夕,清源上线了一个名为“记忆之桥”的新功能。用户可以选择将自己的某段录音设为“遗嘱级私密档案”,指定一位或多位继承人在特定条件下解锁??比如十年后、亲人去世后、或本人失联超过三十天。
第一条被设定为此类档案的,是一位患有渐冻症的维吾尔族音乐教师阿布都拉。他在视频留言中说:“我可能很快就不能说话了,但我想让我的女儿知道,爸爸一直以她为荣。哪怕她选择了一条我不理解的路。”
这项功能引发了短暂争议,有人担心会被滥用或成为情感勒索工具。但在一次公开听证会上,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含泪陈述:“我儿子走之前最后说的话是‘妈,对不起’。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道歉。如果那时候有清源,也许我能听到更多……也许我能告诉他,你不需要对不起任何人。”
最终,该功能以微弱优势通过伦理审查,并附带严格的多重验证机制。
夏天来临前,教育部正式宣布将“情感表达能力”纳入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国1500所中小学。与此同时,清源团队收到一封来自新疆喀什的信,署名是“一群奶奶”。
信中写道:“我们年纪大了,不太会用手机。但我们听说,只要录下声音,就能传给孙子孙女。所以我们凑钱买了个录音笔,轮流讲过去的故事。有打仗的,有逃荒的,也有恋爱的。我们不知道这些有没有用,但我们想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只会唠叨的老太太,我们也曾年轻过,爱过,痛过。”
周望看完信,眼眶湿润。她立即协调技术团队开发“银发之声”专项通道,简化操作流程,支持方言自动转写,并为老年用户提供一对一远程指导服务。
半年后,这个频道累计收录了超过八万条来自六十岁以上老人的口述历史,其中近三成涉及家族创伤、战争记忆或未竟心愿。一条来自甘肃农村老太太的录音尤其动人:
>“我十八岁那年被人贩子拐卖到山西,整整逃了七次才成功回家。可回到家,我妈说我‘脏了’,不让我进祠堂。我这辈子没敢跟任何人提这事。现在我都七十了,孙子问我小时候有没有故事,我就想试试……我说出来了,心里这块石头,好像轻了一点。”
这些声音没有掀起舆论风暴,也没有成为热搜话题。它们安静地躺在服务器深处,像冬眠的种子,等待某一缕春风唤醒。
年底,“诚实之夜”迎来第二届。这一次,不仅有学生参与,还有警察、医生、外卖员、环卫工人……各行各业的人们在零点时刻同步上传了自己的“心情快照”。
有一条来自武汉的护士:“抗疫三年,我从没哭过。但昨天路过幼儿园,听见小朋友唱儿歌,我突然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我不是脆弱,我只是……太想我女儿了。”
还有一条来自深圳的农民工父亲:“我打工二十年,每年只回家两次。今年春节,我儿子给我发了个红包,写的是‘爸爸辛苦了’。我拿着手机看了两个小时,不敢点开,怕看到金额太小伤他自尊。”
最让人动容的是一条儿童临终关怀病房里的录音:
>“医生说我的病治不好了。我不怕死,但我怕忘了妈妈的样子。所以我每天都在录音,记下她说话的声音、做饭的声音、走路的声音……将来我想她的时候,就可以听听。妈妈,你要答应我,也要好好活着。”
这条录音后来被一位作曲家用AI合成技术谱成了钢琴曲,命名为《听妈妈的脚步声》,在次年的国家大剧院公益演出中首次演奏。
周望坐在台下,泪水滑落。
散场后,她给林昭发了条消息:“我们做的从来不是拯救,是陪伴。”
林昭回复:“而陪伴,是最长情的抵抗。”
新年钟声再度敲响时,全球清源用户的私密录音上传量再次突破峰值。数据中心的日志记录下这样一句话:
>“人类最勇敢的行为,不是战胜恐惧,是在恐惧中依然选择说出真相。”
周望这一年依旧奔波在全国各地的试点学校之间。她不再追问“这个项目能不能改变世界”,而是学会问每一个孩子:“你想对这个世界说什么?我在这里,愿意听。”
她知道,有些伤口永远不会愈合,有些遗憾永远无法弥补。但她也明白,只要还有人愿意开口,就有希望留存;只要还有人愿意倾听,就有温暖传递。
某夜,她在川西高原的一所寄宿制学校宿舍里批改成长日志,窗外星空如海。一个小女孩悄悄递给她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
“老师,我今天录了音,说我喜欢同桌。他说他也喜欢我。我们约好明年一起参加校园歌手大赛。”
周望笑了,把纸条夹进笔记本。
那一刻,她忽然懂了艾山医生临终录音的意义。
有些话,趁还能说,就说出来。
因为爱,不该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