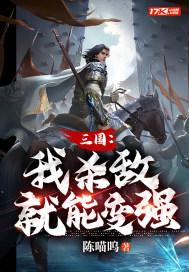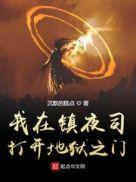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财富自由从毕业开始 > 第650章 动物世界(第2页)
第650章 动物世界(第2页)
每听一遍,周望的心就往下沉一分。
傍晚六点,车子终于抵达泉吉乡小学。心理老师才仁卓玛已经在等她。这位三十出头的女教师双眼通红,手里攥着一张纸条:“我们找到了她留下的字条,说要去湖边看星星,再也不回来了。”
“青海湖现在零下十几度,湖面部分结冰,但边缘还有裂口。”才仁卓玛声音发抖,“她穿的是单薄的校服外套。”
两人立刻联系乡派出所,但由于暴风雪预警,警力有限,最快也要两小时才能派出搜救队。
“等不了。”周望抓起手电筒,“我知道她会去哪儿。”
她记得在项目调研时听过当地人讲,青海湖西岸有一处被称为“月亮湾”的浅滩,传说逝去的灵魂会在满月之夜从那里渡向彼岸。许多情绪崩溃的年轻人曾在那里留下足迹。
风雪中,她们徒步前行。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呼吸都带着血丝的痛感。走了近一个小时,终于在一片灰白色的冰面上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
卓玛吉蜷缩在一块岩石后面,双手抱着膝盖,脸冻得发紫,但还醒着。她的录音笔放在身旁,屏幕上显示着正在录制的状态。
周望慢慢靠近,蹲下身,轻声说:“你在录吗?”
女孩抬起眼皮,眼神空洞地看着她。
“我可以听吗?”周望问。
过了几秒,卓玛吉点了点头。
周望按下播放键。里面传出她自己的声音,断断续续:
>“我恨我自己……我不该出生在这个家。爸爸说我是个赔钱货,还不如死了……我说我想读书,他说女孩子读再多也没用……昨天我数学考了全班第二,他把试卷撕了,说别装好学生,迟早嫁人算数……”
声音到这里停顿了很久,然后是一阵压抑的抽泣。
>“可是……我还是想活下去。我只是……太累了。我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睡一觉……”
周望听完,没有说话,而是打开了自己的手机,调出一段音频:“我能给你听一个人的故事吗?”
那是清源数据库里一段授权公开的录音,来自云南怒江的一位傈僳族少女娜阿朵。她在十五岁那年因家庭暴力多次尝试轻生,最后一次被救回来后录下了这段话:
>“那天我站在悬崖边,风吹得我睁不开眼。我想跳下去,这样一切就结束了。可就在那一刻,我听见广播里放起了爷爷生前最爱唱的调子。那是他教我的第一首歌。我突然想,如果我跳下去,谁来唱这首歌给下一代听呢?”
音频结束,周望看着卓玛吉:“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录‘心情快照’时说了什么吗?”
女孩微微摇头。
“你说:‘今天我学会了唱一首新歌,虽然跑调了,但我敢唱给别人听了。’”周望轻声说,“你知道吗?那段录音被选入了‘火焰计划’的年度精选,已经有三千多个孩子听过,他们说,因为听了你的声音,他们也敢开口了。”
卓玛吉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你不是累赘,你是某个人未来的光。”周望握住她的手,“你现在愿意跟我回去吗?我们可以一起录一条新的‘心情快照’,告诉这个世界:我还在这里。”
风雪渐歇,远处传来搜救队的呼喊声。才仁卓玛脱下棉衣裹住女孩,一行人缓缓踏上归途。
三天后,卓玛吉在心理辅导室重新录制了一段音频:
>“我本来以为,只有死才能让痛苦停止。但现在我知道,说出来,也能让痛苦变轻。谢谢那个冒着风雪来找我的姐姐,也谢谢所有听过我声音的人。我不是失败者,我是幸存者。我会继续唱歌,哪怕跑调。”
这条录音被系统标记为【心理韧性重建完成】,并自动推送至全国试点学校的教学案例库。
与此同时,赵晓禾从联合国归来后,正式启动“清源?边境计划”??将技术模块适配至全国23个陆地边境县的双语学校,特别针对跨境民族家庭的语言断裂、身份认同困境进行干预。第一批接入的包括塔吉克族、哈萨克族、傣族聚居区的四十七所学校。
而在成都,林昭带领团队完成了“代际对话工作坊”的标准化手册编写,并与中央民族大学合作开设相关课程。越来越多的社区中心开始申请引入这一模式,甚至有监狱系统提出希望用于服刑人员的家庭修复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