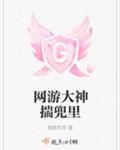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重燃青葱时代 > 第878章 小王子与玫瑰(第2页)
第878章 小王子与玫瑰(第2页)
当晚,袁婉青独自坐在办公室,重播这段视频。她注意到,每当有孩子开口说话,陈默都会轻轻点头,动作细微却充满肯定。她忽然明白,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灌输答案,而是守护提问的权利。
凌晨一点,她正准备关机,邮箱提示音响起。附件是一份PDF文档,标题为《致海风邮局全体志愿者的一封公开信》,署名“一群正在学习倾听的人”。
她点开阅读:
>“我们是市重点中学‘共情教育实验班’的学生。过去一个月,我们走访了六所外来务工子弟学校,收集了89封无法寄出的信。我们才知道,原来同一个城市里,有人每天走四公里上学,有人为了省饭钱只啃馒头,有人因为口音被同学嘲笑‘像乡巴佬’。
>我们曾以为苦难离我们很远,直到我们真正听见。
>现在,我们请求加入‘代笔行动’,并倡议设立‘倾听日’,每月第一周周五,所有班级开放十分钟匿名倾诉时间。
>我们不知道能改变多少,但我们想试试,让校园不再有沉默的角落。”
袁婉青读完,眼眶发热。她立即转发邮件给核心团队,并附言:“同意立项。资源支持全部到位。”
第二天中午,苏念和田穗带着施工队来到邮局后院。他们开始挖掘“树根计划”的基坑,深度要求一米八,象征“触及灵魂的深处”。苏念亲自监工,连水泥配比都要亲手检查。田穗则在一旁绘制地面雕塑的设计图,每一根金属枝条的位置都经过精确计算,确保阳光照射时能在地面投下“心形”光影。
袁婉青站在廊下看着,忽然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回头一看,竟是王小舟,怀里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
“姐,”他笑着说,“我把以前拍的照片全带来了。全是你们做志愿者这些年的事。有阿杰在暴雨中护送孩子回家,有唐果蹲在地上教小女孩折纸船,还有你……站在路灯下读一封信,背影都被雨淋湿了。”
袁婉青怔住:“你什么时候拍的?”
“很多年了。”王小舟轻声说,“我一直觉得,这些画面不该只存在记忆里。我想办个摄影展,名字就叫《听见》。”
她望着他,忽然意识到,这个曾经叛逆、逃学、差点走上歧路的少年,如今竟成了最坚定的见证者。她用力点头:“好,就在‘树根计划’揭幕那天开展。”
一周后的清晨,邮局迎来了一场特别仪式。林小树的母亲作为首位“家属代表”,亲手将第一片信纸碎片投入基坑。紧接着,三十一名志愿者依次上前,放入各自珍藏的信件复制品??有的是孩子画的全家福,有的是失联多年后重逢的合影,有的只是简单一句“谢谢你听我说”。
当最后一片纸落入土中,苏念启动预设程序。地面雕塑内部的LED灯缓缓亮起,暖黄色光芒顺着金属枝干向上蔓延,最终点亮整棵树冠。与此同时,U盘中的音频自动播放,上百个孩子的声音交织响起:
>“我想妈妈了。”
>“我考了全班第三。”
>“我不怕黑了。”
>“我也想帮助别人。”
声音如风拂过,掠过屋顶,穿过街巷,传向远方。
仪式结束后,袁婉青回到办公室,发现桌上多了一封信。没有信封,纸张普通,字迹稚嫩:
>“袁老师:
>我是周岩。昨天社工姐姐带我去看了新宿舍,有床、有书桌,还有窗。她说以后每周都有心理老师陪我聊天。
>我把那封回信贴在墙上,每天醒来都能看到。
>你说得对,我不是灾祸。我是幸存者。
>下个月,我想报名参加‘倾听角’培训,学着给别人写回信。
>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她读完,轻轻将信夹进《倾听手记》的最后一页。窗外,夕阳正缓缓沉入城市天际线,余晖洒在门楣灯笼上,映出一片温暖的橙红。
夜里十点,她最后一次巡视邮局。信箱已被清空,录音机归位,打印机待机指示灯安静闪烁。她站在门槛上,仰望星空,忽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歌声??是孩子们自发组织的夜诵活动,他们在朗读一封集体创作的信:
>“我们知道世界很大,黑暗很多。
>但我们也要告诉它:
>这里有一群不肯闭嘴的孩子,
>有一盏永不熄灭的灯,
>还有一阵,永远向着光奔跑的风。”
袁婉青闭上眼,任晚风吹乱鬓角碎发。她知道,这场漫长的倾听不会结束。它只会不断生长,像一棵扎根于无数伤痕与希望之上的大树,在无人注视的角落,悄然撑起一片可供喘息的阴凉。
她说不出更多话,只能再次轻声呢喃:
“你说,我听着。”
这句话,落在泥土里,长成了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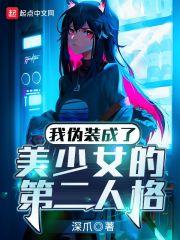
![每个剧本都要亲一下[快穿]](/img/3617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