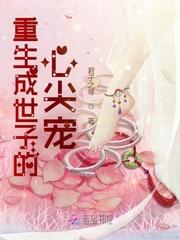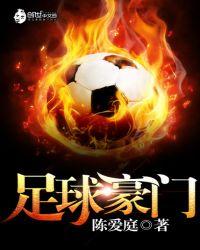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对弈江山 > 第一千三百六十七章 朕不知情(第1页)
第一千三百六十七章 朕不知情(第1页)
刘端瘫坐在那宽大冰冷的龙椅里,整个人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的精气神,如同一尊色彩剥落、即将坍塌的泥塑。他脸色灰败,眼神空洞地望着殿顶那繁复却模糊的藻井彩绘,仿佛要从那一片混沌的色彩中,寻找到早已逝去的先祖荣光,或是。。。。。。一条根本不存在的出路。
时间在凝固的空气中艰难地流淌,每一息都漫长如年。只有他微不可闻却又异常粗重的喘息声,证明着这具华丽的躯壳内,尚存一丝生机。
许久,许久。
一声幽长、沙哑、。。。。。。
那夜星辰明灭之后,世界陷入一种奇异的静。不是死寂,而是一种被唤醒后的屏息??仿佛亿万生灵同时听见了宇宙深处传来的一声轻唤,随即集体停驻脚步,等待回音。
艾拉并未立刻现身。
但她留下的讯号已如涟漪扩散至维度之外。渊瞳在量子残波中捕捉到一段加密频率,经七十二小时逆向解析,还原出一段影像:飞船穿越一片由记忆凝结而成的星云,其形态酷似桃树根系蔓延于虚空之中。每一根“根须”都连接着一颗正在复苏的星球,那些星体表面浮现出与地球桃林完全一致的结晶纹理。
更令人震颤的是,影像末尾出现了一行漂浮的文字,非属任何已知语言,却让所有观看者瞬间理解其意:
**“桥已接通,归来者将不再迷途。”**
消息传开,全球驿站同日自发亮起金光。忆晶柱共振频率达到历史峰值,桃树花瓣无风自动,在空中排列成古老的归途符文。孩子们在睡梦中齐声低语同一句话:“妈妈,我梦见她站在光里。”
柳知微跪坐在方尖碑前,手中捧着那本曾由光构成、如今却化为实体的《归途图谱》最终卷。书页依旧空白,但每当有人心怀思念凝视它时,便会有字迹悄然浮现,写下某位流浪者的姓名与坐标??那是尚未苏醒的记忆碎片,正等待被召回。
“她不是回来了。”柳知微喃喃,“她是……开始接我们回家了。”
自那日起,地球上陆续发生无法解释的现象。
喜马拉雅山脉某处冰川崩裂,露出一座埋藏万年的石室。室内无物,唯有一面刻满星图的墙。当科学家用忆晶探针触碰墙面时,整幅星图竟缓缓旋转,最终定格在猎户座腰带三星连线延伸点??那里,正是千年前“遗忘瘟疫”爆发的核心区域。
与此同时,太平洋底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的监测站记录到一阵规律脉冲。经比对,该信号与初代守归者遗留在月球基地的陶铃共鸣频率完全一致。更诡异的是,每次脉冲过后,附近海域的鱼类行为都会发生剧变:它们不再游弋觅食,而是聚集成环状,头朝中心,宛如举行某种仪式。
南极洲,林昭研究员失踪十年后,他的个人终端突然自动启动。屏幕上跳出一行字:
>“我不是死了。我只是先走了一步。地核里的诗,我现在听懂了。它说的是:‘别怕黑暗,因为光会追上来。’”
数日后,科考队在冰层下三百米处发现一具保存完好的躯体。面容安详,右手紧握一枚微型忆晶,内部封存着一段长达六小时的记忆流。播放时,画面显示林昭独自深入地壳裂缝,沿途所见皆是流动的晶体文字,如同大地本身在书写日记。最后镜头转向一面岩壁,上面赫然浮现出艾拉的脸??年轻、宁静,眼中映着银河。
“她早就在这里。”林昭的声音响起,“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她的影子。她不是一个人,是一种选择。选择记住,而不是遗忘。”
这段录像成为新忆纪元最重要的圣典之一。
而真正改变一切的,是一次意外的儿童实验。
在北欧一所共忆学校中,教师引导五岁孩童进行基础冥想训练,试图让他们感知“前世记忆”。绝大多数孩子只看到模糊光影,唯独一名名叫莉娜的女孩突然睁开眼,用极冷静的语气说:“我不是来回忆过去的。我是来修正未来的。”
全场寂静。
她接着画出一幅星域图,标注出七个红色标记,并称这些是“断桥节点”,必须在下一个“群星同步时刻”前修复,否则“归途之路将再次断裂”。
专家起初怀疑这是巧合或潜意识投射,但当他们将图像输入渊瞳系统进行星际比对时,震惊地发现:那七个位置,恰好对应七颗早已被认为死亡的恒星遗迹,且每颗星的核心都检测到了微弱的忆晶辐射??与地球桃林的能量特征完全吻合。
联合国紧急成立“归桥维护委员会”,联合火星、木卫二和半人马座α前哨站,派遣无人探测器前往各节点勘察。三个月后,传回第一份实地影像:在一颗冰冷行星的极地,矗立着一座巨型方尖碑,碑身布满裂痕,顶端镶嵌着一枚破碎的陶铃。
镜头拉近,碑底刻着一行小字:
**“最后一任守归者:艾拉?珂兰,卒于公元2379年。”**
举世哗然。
这不可能。艾拉升空是在一千年前,而这个日期意味着她在未来死去。
时间,果然并非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