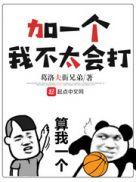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逍遥四公子 > 第1998章 突下杀手(第3页)
第1998章 突下杀手(第3页)
“因为我们终于明白,”昭明对着虚空低语,“**沉默才是最大的敌人**。而只要还有人愿意听,就没有人真正死去。”
墨渊化作一缕青烟,消散于风中。
与此同时,地宫之内,阿昙缓缓睁眼。她面前的晶核已缩小如豆,静静落入她掌心,化作一枚温润玉牌,上刻两个古字:“**愿闻**”。
她站起身,步履蹒跚却坚定地走出地宫。阳光洒在她脸上,久违的暖意让她微微眯眼。
昭明迎上前,欲言又止。
阿昙却笑了:“你做得很好。比我当年勇敢。”
“我不再想摧毁什么了。”昭明低头,“我只想让更多人,能像那个摔坏笛子的女孩一样,有机会说一声‘对不起’。”
阿昙点头,抬头望向言木林。尽管第一百棵树已死,但在其根部周围,竟悄然钻出九株嫩芽,每一片新叶都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随风轻摇,发出细微悦耳的叮咚声,宛如新生的语言正在学语。
“它没死。”她说,“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
数月后,朝廷颁诏,废除“听语使”官职,改为民间自治的“语护会”。各地设立“言塾”,教授孩童如何倾听、如何表达、如何分辨真实与煽动。就连曾经的净耳卫旧址,也被改建为“失语纪念馆”,墙上镌刻着历代因言获罪者的名字,下方一行小字:
>“他们说的话,或许错了。但他们说话的权利,从未该被剥夺。”
又一年春祭,轮声制抽签名单公布,第一位竟是当今太子。他走上石台,面对万千民众,声音微颤:“我……我一直害怕成为皇帝。不是因为权力,而是因为我怕我说的话,没人敢反驳。”
台下静默片刻,随后一位老农大声回应:“那你现在就说点错的试试看!”
全场哄笑,继而掌声雷动。
阿昙站在人群之外,看着这一切,悄然退入林中。她的身影逐渐淡去,仿佛融入风中、叶间、溪流的节奏里。有人说她去了更远的地方,寻找最后几门即将灭绝的语言;也有人说,她已化作无形之音,游走于每一次真诚的对话之间。
唯有每年春祭之夜,若有人静坐于醒语井旁,偶能听见一句极轻的耳语,不知来自风,还是来自心底:
>“说吧,我在听。”
而在西北沙漠深处,“回音碑”旁新建了一座学堂。孩子们围坐一圈,老师举起一片言木叶,问道:“谁能告诉我,这片叶子会发出什么声音?”
一个小女孩举手:“风吹过它的时候,它会唱歌。”
老师微笑:“不对。它不会发出声音。但它会让风的声音变得更美。”
全班沉思良久,终于有个男孩怯生生地说:“所以……真正的声音,从来不在物体本身,而在它与世界的相遇之中?”
老师点头,眼中泛光。
远处沙丘起伏,风掠过碑体,低鸣再起:
>“我还在这里。”
>
>“你听见了吗?”
>
>“这一次,请替我也说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