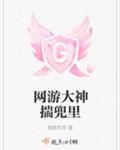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逍遥四公子 > 第1999章 金藤虫(第1页)
第1999章 金藤虫(第1页)
宁宸骇然,这可是柳白衣斩出的剑气,迅疾凌厉。
唰!!!
关键时刻,残梦出鞘。
可就在他挥剑时,突然间肩头一紧,一只手将他拉到了身后。
是老天师。
老天师一手将宁宸拎到身后,另一只手同样是剑指一挥,剑气激射而出。
“轰”的一声!
两道剑气在半空碰撞,让那片空气出现严重扭曲。
“柳小子,你怎么回事?”
老天师沉声问道。
风沙掠过回音碑的裂痕,将最后一句低语卷向天际。那声音轻得几乎不存在,却又固执地在旷野中流转,像一缕不肯消散的魂。西北的夜来得极快,夕阳刚沉入沙海,星辰便已密布苍穹,仿佛无数双眼睛俯视人间。学堂里油灯摇曳,孩子们围坐一圈,手中捧着用言木叶制成的小铃铛??这是他们亲手做的“语种器”,据说只要诚心许愿,摇响它时,远方的人就能听见心声。
老师姓白,曾是净耳卫末代副使,如今两鬓斑霜,却眼神清亮。他轻轻抚摸那片被供在讲台上的言木叶,低声说:“你们知道吗?这片叶子原本不会响。可自从阿昙小姐让沉默之种安眠后,所有与言语有关的东西,都开始有了回应世界的可能。”
小女孩眨着眼睛问:“那它现在唱歌了吗?”
“不。”白老师摇头,“它依旧无声。但它学会了震动风,就像人学会倾听之前,必须先承认自己并不全知。”
男孩忽然举起手:“老师,如果我说的话没人听呢?如果我说了错话,会被割耳朵吗?”
教室一时安静。几个年幼的孩子下意识摸了摸耳垂,那里还留着旧制烙印的淡痕。
白老师起身,从箱底取出一块铜牌,上面刻着“愿闻”二字。“这是一位叫昭明的大人送来的信物。”他说,“他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哪怕你说错了,也依然有人愿意听完。”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稚嫩的脸:“从前,我们怕说话;后来,我们怕说错话;现在,我们要学的是:**即使害怕,也要开口**。”
窗外,风穿过碑隙,发出悠长叹息。
而在千里之外的东海渔村,晨雾未散,一艘破旧渔船正缓缓靠岸。船头站着个披蓑衣的老渔夫,怀里抱着一只陶瓮。瓮身布满裂纹,却被金漆细细修补过,隐约可见“醒语”二字。他是当年九支远征队中唯一幸存的成员,名叫陈七,曾因私自传诵《万语谱》残章被剜去半只舌头。如今他已不能完整发音,说话如风吹枯芦,沙沙作响。
但他每天清晨都会来到这座新建的“语亭”,把陶瓮放在石台上,然后盘膝而坐,用手势比划着一段段古老渔歌。旁边有个失聪少女,名唤阿荇,正专注地看着他的动作,指尖随节奏轻敲桌面,将那些无法出口的声音翻译成文字,抄录进一本牛皮册子里。
这本册子名为《哑音集》,收录的全是未曾被听见的语言:盲者的梦境低语、囚徒指甲刮墙的节奏、战马临死前鼻息的顿挫……甚至包括一种只存在于手势间的家族密语,传承了十七代,险些随最后一位老人离世而湮灭。
今日,阿荇翻到一页空白,抬头问道:“陈伯,您还记得小时候母亲哄睡您的那首歌吗?”
老人怔住,眼中泛起水光。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调子,只能颤抖着双手做出环抱婴儿的动作,轻轻晃动身子,喉咙里挤出断续的“嗯……啊……哦……”。
阿荇闭上眼,静静感受那不成旋律的哼鸣,良久,提笔写下:
>“月儿走,娘在守,
>风不来,我不走。
>你睡吧,梦里没有网,
>只有浪花亲你额头。”
写罢,她轻声念出。老人猛地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这是他母亲五十年前唱过的歌,他自己早已遗忘,却在女儿般的少女口中重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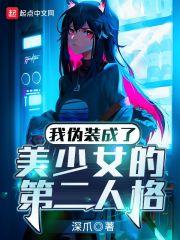
![每个剧本都要亲一下[快穿]](/img/3617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