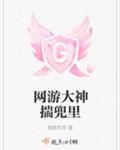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嘉平关纪事 > 2512 老当益壮108 0(第1页)
2512 老当益壮108 0(第1页)
“这还是很正常的吧?说明他们对这些孩子是真的上心了,只有上心了,真心想要培养他们,才会要求比较高,比较严厉,不是吗?”金苗苗一只手托着腮帮子,另外一只手在桌子上没意识的画圈,“我们小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风雪停了三日,嘉平关外的荒原上浮起一层薄雾,像是大地吐纳的余息。那座无字碑静静立在雪中,表面凝着细霜,仿佛从未被触碰过。可若有人俯耳贴近碑底,便会听见极轻的呢喃,如风吹经幡,似雨打残荷??不是诅咒,也不是召唤,倒像是一段终于得以安放的记忆,在低语着某个名字:**沈茶**。
这个名字早已不刻于史册,也不存于玉牒。但在辽东边境的一处小驿里,仍有人会在夜深人静时默念它。
陈归坐在火塘边,手中摩挲着那块泛黄的襁褓布片。十年过去,他不再是当年那个被批为“来历不明”的年轻斥候,而是如今镇守北境的副将。朝廷推行“新民策”后,他正式改名“沈归”,取“归来”之意。没人再问他的出身,也没人敢提那半个模糊的“沈”字。可他知道,自己从未真正离开过那个谜团。
今夜,他又梦见了那片银杏叶。
梦中,沈拾站在敦煌千佛洞前,背影单薄如纸。他回过头,没有说话,只是将一枚断银针轻轻放在石阶上。陈归想上前拾起,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耳边响起童谣声:
>“风吹沙,不问家,
>浪打舟,岸自斜。
>若问吾名何处起,
>笑指心头那朵花。”
歌声未落,整座石窟轰然坍塌,化作飞灰。而那根银针,竟随风飘至千里之外,落在他掌心,温热如血。
他惊醒过来,冷汗浸透衣襟。
窗外月色惨白,照见案头一封刚送达的密信??并非军报,而是来自江南安心堂的传书。信纸素净,只写一行小字:“**你母亲临终前说,她记得梅花开时,你在哭。**”
陈归的手猛地一颤。
他从不知道自己有母亲。戍卒们只说他在战火中被人遗弃,襁褓裹着半片绣梅布条,便由众人轮流抚养。可这封信……是谁写的?安心堂又怎会知道这些?
他立刻命人备马,不顾风寒,连夜启程南下。
与此同时,江南水乡正逢春汛。老塾师已年逾八旬,不再授课,每日只在院中种梅、煮茶。那间曾传出“心安即是吾乡”的学堂,如今成了村中孩童嬉戏之所。唯有黑板上的四个大字依旧清晰,墨迹似永不褪去。
这一日清晨,他推开窗,见一只银蛾停在梅枝上,翅膀透明如琉璃。他并不惊讶,反而微微一笑,取出笔砚,铺纸研墨。
银蛾振翅,落入砚台,化作一点微光,渗入墨中。
他提笔写下一封信,字迹苍劲却温柔:
>“归儿:
>我非你生母,亦非知情之人。但我曾见一位女子抱着婴儿跳入湖中,口中唱着童谣。她穿白衣,盲眼,腕上缠着一根银线。我救下了孩子,那是你。
>她说,‘只要有人记得这首谣,就还有希望。’
>如今,我希望到了。
>不必寻根,不必复仇。
>你活着,便是她的答案。”
信末署名仅一字:**箬**。
他吹干墨迹,放入竹筒,系于一只白鸽脚上,放飞而去。
数日后,陈归抵达安心堂。堂前匾额高悬“不查即是慈悲”,门庭若市,皆是前来求治“心疾”的百姓。有人因家族纷争而疯癫,有人因身份质疑而自残,更有士族之后跪地痛哭,说自己一生都在害怕“不是真的”。
堂主是一位年轻医师,正是当年手持断银针唤醒瘟疫病人的流浪郎中。他迎上前,未语先笑:“你来了。”
陈归一怔:“你认识我?”
“你不认得我,但我认得你。”医师从怀中取出一枚铜牌,上面刻着清源司旧印,“我是崔九之子。我父临终前说,若有一日‘风吹沙’之谣传至辽东,便说明那人已经开始苏醒。”
“什么苏醒?”
“不是肉体,是执念。”医师目光沉静,“你以为‘雪鸠’死了?它只是换了形态。从前它藏于血脉之争,如今它潜入人心之疑。每一个怀疑自己是否‘够格’的人,都是它的养分。”
陈归沉默良久,终将那封竹筒信递出。
医师读罢,轻叹一声:“阿箬先生……原来她还活着。她是柳如月的师妹,也是唯一一个看破‘梦渡之术’真相的人。她知道,真正的封印不在地底,而在人心愿不愿放下追问。”
“所以沈拾……真的死了?”
“我不知道。”医师摇头,“那一夜,七盏灯燃尽,壁画崩裂,我们找到的只有染血的衣袍和熄灭的油灯。但他留下的童谣,已在千万人口中传唱。当一个人开始相信‘我是我’,‘雪鸠’便无法寄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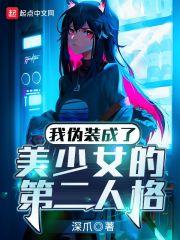
![每个剧本都要亲一下[快穿]](/img/3617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