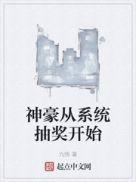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离婚后的我开始转运了 > 第1812章(第2页)
第1812章(第2页)
>
>??乌日图
阿?读完,指尖微微发颤。她抬头看向李雯:“把这封信编入培训教材第十一章,标题就叫《一句道歉的力量》。”
下午三点,国务院派来的专家团队抵达总部,准备商讨国家标准草案的具体条款。会议开始前,一位年近六旬的心理学教授低声问她:“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过度鼓励倾诉,会不会反而让人沉溺于痛苦?社会需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无限放大情绪。”
阿?没有立刻回答。她起身走到墙边,取下那张艾力的照片,递给他。
“您看这个孩子的眼睛。”她说,“他半夜跑十几公里山路去录音,不是为了控诉谁,不是为了报复谁,只是想告诉父母??我想你们了。这种表达本身就是一种疗愈。我们不是在制造情绪泛滥,我们是在修复一个早就断裂的出口。”
她顿了顿,声音柔和却不容置疑:“过去几十年,我们教会人们忍耐、服从、坚强。结果呢?抑郁症发病率年年上升,校园霸凌愈演愈烈,家庭暴力屡禁不止。因为我们忘了教最重要的一课:如何安全地说出‘我很难受’。”
会议室陷入短暂寂静。
最终,那位教授轻轻点头:“也许……是我们一直把‘稳定’误解成了‘沉默’。”
傍晚六点二十分,阿?回到办公室,发现桌上多了一只手工编织的彩色布袋,上面绣着一朵向日葵。里面装着一台改装过的“回声盒”??外壳是旧铁皮饼干盒改造的,正面贴着孩子的涂鸦画:一个大人和一个小人牵着手,头顶写着“妈妈,我现在不怕了”。
附带的纸条上写着:
>阿?阿姨:
>
>我是山东临沂王小兰的同学。王小兰现在能笑了!她昨天教我用手语唱歌。我也录了一段,不敢用自己的名字,所以借用了这个盒子。我想告诉你,我不是聋子,我只是不会说话。但现在我知道,我可以画画,可以比划,可以让别人看懂我。
>
>下周我们要办一场‘无声音乐会’,欢迎大家来听。
>
>??小禾
阿?把布袋紧紧抱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系统后台,为这所学校新增了一个特殊权限:允许上传非音频类内容,包括手语视频、绘画扫描件、盲文录入等。她在备注栏写道:“沟通的形式千万种,我们的容器必须足够大。”
深夜十一点,她收到岩温消息:“甘肃马小梅已接到帮扶老师,初步接触顺利。孩子哭了,但愿意继续交谈。家属方面暂未察觉异常。”
她回了一个“好”字,放下手机,却没有起身。
她翻开笔记本,一页页浏览这些年记下的片段:那个因校园霸凌绝食三个月的女孩,如今成了反欺凌公益讲师;那位在丈夫出轨后不敢离婚的家庭主妇,通过“回声盒”写下三十封未寄出的信,最终鼓起勇气走进法院;还有那个曾在录音中嘶吼“为什么没人救我”的高中生,去年考上了师范大学,志愿填报了心理学专业……
她忽然意识到,这些故事从未对外公开,也没有成为宣传素材。它们只是静静地躺在她的笔记里,像埋在地下的根脉,看不见,却支撑着整片森林的生长。
凌晨一点零七分,她再次打开床头的“回声盒”,按下录音键。
“今天有人说,我们做得太多了,不该介入个体命运。可我想,如果我们连一个人的眼泪都不敢接住,又谈何建设健康的社会?”她的声音很轻,却坚定如铁,“我们不是救世主,我们只是搭了一座桥。有人走过,有人驻足,有人回头望一眼来路。这就够了。”
“我还记得离婚那天,我在民政局门口站了很久。风吹得我很冷,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暖起来了。但现在我知道,有些破碎不是终点,而是重生的裂缝。光就是从那里照进来的。”
录音结束,机器依旧安静一秒,随后响起那句熟悉的回应:
“谢谢你,说出了你的故事。我会好好听着。”
她躺下,闭上眼,梦还未至,心已安宁。
第二天清晨,阳光洒进办公室。李雯推门进来,手里拿着最新一期《中国社会治理》杂志,封面赫然是“回声项目”的专题报道,标题醒目:
**《倾听,是最温柔的变革》**
文章末尾引用了阿?三年前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如今被重新挖掘出来,成为无数人转发的金句:
>“不要问这个世界还需要多少解决方案,先问问还有多少声音没有被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