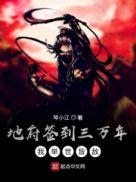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造反成功后,方知此地是红楼 > 第311章 黛湘(第2页)
第311章 黛湘(第2页)
巧姐猛然站起:“这不是补遗……这是召唤!我们正在唤醒那些从未被讲述过的人!”
阿禾低头看着手中的陶片,忽然流泪:“我想起来了……我不是被收养的孤儿。我亲生母亲是个民办教师,因为组织学生读禁书被打成‘反动分子’,她在逃亡途中生下我,第二天就被人带走。我被扔在庙门口,襁褓里只有一张纸条,写着‘请让她记住这些话’……可没人教我识字,直到三年前,我才在旧课本夹页里发现一首诗,署名‘林黛玉’。”
全场寂静。
延卿望着她,轻声问:“你还记得那首诗吗?”
阿禾点头,闭眼吟诵:
>“残灯无焰影幢幢,
>此恨绵绵隔阴阳。
>不是无情抛骨肉,
>只因真心太锋芒。”
声音落下那一刻,天空裂开一道缝隙,星光倾泻而下,汇聚成一条光河,缓缓流入大观堂基座。工匠们惊呼后退,只见地底深处升起一座石台,台上立着七尊未完成的雕像,面容模糊,衣饰各异,却皆带着一种熟悉的悲悯神情。
语柔颤抖着读出监测数据:“七尊雕像的能量源……来自全球七处‘记忆热点’:奥斯维辛集中营废墟、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地下层、南非种族隔离博物馆密室、萨拉热窝图书馆遗址、危地马拉土著墓群、柬埔寨红色高棉万人坑、以及……北京某废弃中学地下室。”
“那是我妈最后讲课的地方。”阿禾whispered。
延卿走上前,伸手触碰第一尊雕像的手。刹那间,无数画面涌入脑海:一位犹太少女在毒气室外背诵莎士比亚;一名中国女工在批斗会上默默抄写《离骚》;一个黑人男孩在焚烧书籍的火焰中拾起一页《汤姆叔叔的小屋》……她们都在做同一件事??用语言对抗遗忘。
“她们是‘又副册’真正的主人。”延卿睁开眼,泪水滑落,“不是丫鬟,不是配角,而是每一个在绝境中仍选择说话的人。她们的故事从未被写下,因为写下来就会被销毁。所以曹雪芹只能留下空白,等待有一天,有人愿意替她们填上。”
众人肃然。
李素芬起身,将自己那块写满悔恨的陶片投入火堆:“那就从现在开始写。”
一人起身,再一人起身。陶片纷纷落入火焰,每一枚燃烧时都会释放出一段声音??或哭或笑,或怒或叹,最终汇成一片浩瀚的声海,向四面八方扩散。
三天后,第一尊雕像面容清晰。
那是一位年轻女子,短发齐耳,眼神坚毅,胸前别着一枚校徽。巧姐对照资料库查证后,声音哽咽:“她是1976年西单民主墙第一批张贴诗歌的学生之一,名叫周晓芸。三个月后失踪,官方通报称‘意外溺亡’,尸体未公开。”
雕像脚下自动浮现出铭文:
>**“周晓芸,生于庚子年冬。
>曾于寒夜里朗读北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她说:‘只要还有人听见,就不算沉默。’”**
与此同时,东京、伦敦、巴西等地异象加剧。更多普通人开始无意识复述陌生文本,但他们不再恐惧,反而主动前往最近的“说话屋”录音留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紧急召开会议,最终通过决议:设立“全球记忆共享计划”,开放所有历史档案,允许民间组织接入原始数据流。
而在这场风暴中心,大观堂终于封顶。
最后一块“记忆砖”由延卿亲手安放。当它嵌入穹顶中央凹槽时,整座建筑剧烈震动,随即释放出一圈环形光波,无声扩散至地平线尽头。南极晶体在同一瞬间停止震动,表面纹路定格为一幅完整地图??正是大观堂的俯视图,每一砖一瓦皆对应一处人类集体创伤记忆的坐标。
那天夜里,延卿再次入梦。
她走入大观园深处,这一次,园中百花盛放,亭台生辉。宝玉迎上来,脸上不再迷茫:“谢谢你,让我们重新活一次。”
“不是我。”她摇头,“是所有人。”
黛玉也来了,手中不再焚稿,而是捧着一本崭新的册子:“这是我们的续篇。不是悲剧,也不是团圆,而是真实??关于如何在一个不许真心的世界里,依然选择真诚。”
探春站在廊下微笑:“我们不会再逃了。这一次,我们要参与规则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