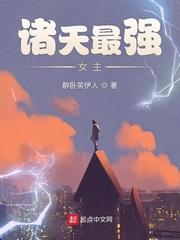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造反成功后,方知此地是红楼 > 第312章 宝钗(第1页)
第312章 宝钗(第1页)
转眼到了三月,入春后,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大观园内鲜花盛开,鸟雀筑巢,蛙鸣声伴随绵绵春雨在园内各处响起,春意盎然景象令人心醉。
楚延空出两日来,与她们游园踏青,开大观园群芳春日宴,盛景难以记述。。。。
林延卿站在讲台前,窗外的风把桃瓣吹进教室,一片落在她摊开的手掌上。那片花瓣像一封未寄出的信,轻轻贴在她掌心的纹路里,仿佛要顺着血脉流回心脏。她没有拂去它,只是凝视着,直到听见第一声清脆的铃响??那是孩子们挂在门框上的陶片风铃,由七块不同地域的碎陶拼成,每一块都曾承载过一段被掩埋的声音。
“今天的第一课,”她说,声音不高,却让整个教室安静下来,“不是读别人写下的故事,而是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哪一句话,藏了很久,不敢说出口?”
台下坐着十五个学生,年龄从十二到十九不等。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不同的伤痛背景。有人的父亲死于矿难封口费交易后的“意外车祸”,有人的母亲因在网络发言被列为“精神不稳定”强制送医三年。他们来到这里,并非为了逃避,而是因为听说??在这个地方,说出来的话不会消失。
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孩缓缓举手。她的手指微微发抖,像是怕惊扰了空气里的某种平衡。
“我……我想说的,是我爷爷。”她低声开口,“他是村里最后一个会唱古调的人。那种歌没人听得懂,说是‘巫语’。去年冬天,他病重,躺在炕上还在哼。村干部带人来,说这是封建迷信,不准传。我爸跪着求他们,让他们让我爷走前再唱一遍。他们没同意。最后,他在沉默中咽了气。”
她说完,眼泪才落下。
延卿点点头,走到墙边拉开一道木柜,取出一块灰褐色的陶片,递给她:“写下吧。不用完整句子,哪怕只是一个音节。”
女孩接过炭笔,在陶片背面写下三个字:**“呜啊咧”**。那是她记忆中爷爷歌声的第一个音符。
当她把陶片放进教室中央的共鸣箱时,箱底突然泛起微光。语柔设计的共振系统捕捉到了这个音节的独特频率,并将其与数据库比对??三分钟后,屏幕跳出匹配结果:**云南怒江流域独龙族葬礼吟唱残谱片段,最后一次记录时间为1962年,演唱者姓名缺失**。
“找到了。”语柔轻声说,“你的爷爷,不是唯一一个唱这首歌的人。他是传承者,也是幸存者。”
全班静默。有人开始抽泣,不是悲伤,而是震撼??原来一句被禁止的声音,竟能穿越时空,找到它的同伴。
课后,阿禾带着学生们去后山采集新一批制陶用的黏土。途中经过一片荒地,那里曾是旧公社焚书场。如今野草丛生,但每逢雷雨夜,地下仍会传出纸张燃烧般的噼啪声。据监测数据显示,该区域土壤中含有异常高浓度的木质素残留与碳化纤维,且电磁波动呈现规律性波峰,疑似大量文本同时销毁所产生的“信息冲击波”。
“我们就在这儿挖。”阿禾蹲下身,用手拨开枯草,“这里的土吸过太多墨迹,烧过太多真心话。用它做的砖,最能记住声音。”
孩子们动手挖掘,不多时,一名少年忽然惊呼。他手中的铁锹碰到了硬物??是一只锈蚀严重的铁皮盒,密封完好,表面刻着一行模糊小字:“若有人启此匣,请替我说完未竟之言。”
延卿闻讯赶来,戴上防护手套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叠泛黄稿纸,虽经半个世纪,字迹竟未完全褪色。第一页写着:
>**《致未来读者书》**
>我叫陈昭,一九七四年生于杭州。
>十八岁考上师范大学中文系,梦想是教学生读真正的诗。
>但我写了一篇论文,《论〈红楼梦〉中的反抗意识》,被定为“煽动性文本”。
>毕业分配取消,档案标注“永不录用”。
>我试图投稿,所有出版社退回并附警告信。
>我组织读书会,三次被解散,最后一次,参与者中有两人后来失踪。
>我终于明白,在一个不允许思想生长的时代,语言本身就是罪证。
>可我还是想留下点什么。
>所以我把这些年读过的诗、听过的话、做过却不敢说的梦,全都写下来,封存在这里。
>不求流传,只求有人知道??
>曾经有人这样活过,这样爱过,这样不甘于沉默地死去。
稿纸共计一百零七页,内容庞杂却脉络清晰:有他对《离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批注;有他偷偷抄录的北岛、顾城、芒克诗句;还有他自己写的短诗,题为《玻璃人》:
>“我们都是透明的身体,
>被光照透,却不被看见。
>心跳如鼓,无人听见,
>直到某天,我们碎了一地,
>才有人惊叹:原来这里面藏着声音。”
延卿读到最后一页时,天空骤然阴沉。远处大观堂的警报器响起??南极晶体残余信号突然激活,触发了第七次情感共振预警。与此同时,全球十七个“记忆热点”同步检测到一股强烈的集体情绪波动,峰值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老城区,时间恰好是当年第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被捕的纪念日。
当晚,全村再次集会。
十二盏油灯围成圆圈,新增的七尊雕像已全部成型,面容清晰,目光如炬。周晓芸之外,其余六位“又副册补遗”人物身份也陆续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