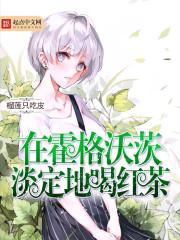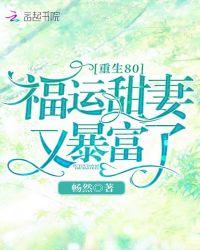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万历明君 > 第254章 黄河上天人头落地(第2页)
第254章 黄河上天人头落地(第2页)
李贵妃坐在皇帝身边,津津有味看了起来,口中不忘宽慰:“陆文裕已然算简朴长者了。”
“喏,陛下你看,二月十五,仅食一餐;十七,疲倦至极,借民居小憩;二十,烧柴取暖,只喝热汤;二十七,市中居民供应汤饼;三月三日,吃豆饭,难以下咽。”
朱翊钧瘪了瘪嘴。
小李要是知道陆家嘴的陆是哪个陆,是决计说不出这种话的。
当然,就陆深本人来说,确实也算不上铺张,哪怕徐霞客那种没官身的,都能靠名望让当地官府主动配备挑山工,更别说陆翰林了。
这待遇放在士大夫里,说是餐风露宿都不为过。
他顿了顿,到底还是说出陆深哪里人烦人:“朕就是烦他视百姓如无物,所谓探访民情,全篇数千字,竟只记了九个字!”
李贵妃闻言,仔细翻看,终于从夹缝里找到关于民情的记载。
三月辛巳,晓发,午过姚店,途见饥民跪,号者相续。
确实只有短短的一行,没什么画面感。
但这算不上陆深的罪过,日录文集都这样写,甚至皇帝这番评语传出去,反而是皇帝刻薄。
不过作为枕边人,李白泱对皇帝反而比外朝多几分了解。
她合上日录,说着体己话:“陛下哪里是烦陆文裕,分明是联想到南巡路上的所见所闻,心中烦闷。”
皇帝前晚回行在的时候就脸色不太对了,陆深显然被恨屋及乌了。
朱翊钧神情一滞,旋即叹了口气。
他顺势枕倒在李贵妃的大腿上:“一半一半吧,士大夫清贵的模样本来就挺烦。”
集体意识是有力量的,也只有看到这些士大夫高高在上的做派,才知道为百姓服务成为“正确”,何其难得——至少骂士大夫脱离百姓,不会反诘说皇帝刻薄。
至于另一半,烦心事可就多了。
朱翊钧连连叹息:“光躲在紫禁城里看奏疏,只觉得欣欣向荣,千好万好,出门一趟吧,这也不好,那也不对。”
“你别看‘饥民跪,号者相续’也就短短几个字,朕偶然间映入眼帘,一天都吃不下饭。”
“一路上的胥吏也不干什么人事,设卡拦税,猖狂至极,李如松这个视察兵备先行官当面,都有人壮着胆子上前勒索。”
“还有,之前路过临朐县的时候,得知有个累世农桑、诗书传家的临朐冯氏,姐姐听过么?”
皇帝躲在后妃怀里,絮絮叨叨说着一路上看到的事。
李贵妃替皇帝理着头发,回忆片刻后答道:“前元万户侯冯才兴的冯氏?听说一度流离到江南,一直到冯裕中进士后,才重返临朐,立起阀阅。”
“而后冯裕、冯惟重、冯惟讷、冯子履,一门四进士,代代不绝。”
“延续两朝而不倒,一度为天下望族传唱。”
到底是世家女子,说起这些如数家珍。
朱翊钧闻言不禁失笑,两朝?太小看人家了。
一门十几个进士,传承有序,明朝倒了人家都不会倒。
到了后清,冯溥照样做文华殿大学士,同治年间更是敏锐转型,让冯桂增做个手握兵权的振威将军,若非天道示警,甚至还能再往后数数。
朱翊钧被阻隔了视线,看不到李贵妃的脸,反问道:“姐姐可知道,坊间百姓是如何唱冯氏的民谣?”
也不待李贵妃回应。
朱翊钧对此自问自答,轻声吟道:“只知临朐有都堂,不知北京有皇上。”
“啧,若不是张辅之点了冯氏的名,让朕到临朐亲自见识了一番,实在不知彼辈如此威风,简直训官府如犬马。”
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对比是很难通过奏疏感受到的。
嘴上念叨着世家望族,可没有亲眼见到来得实在。
朱翊钧将头从大腿上往外拱了拱,好对上李贵妃的视线:“说到这个,还是僧道常怀敬畏,时时不忘称量朕的面子。”
“姐姐还记得,朕六年前曾与僧道约法三章,遏制高利贷的事么?”
六年前,他巡视北直隶期间,顺道将高利贷收拢到户部账下监管。
甚至并未限制太多,只是要求到户部备案、框定出一个利息上限、不许利滚利三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