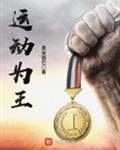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高武:陪练十年,一招出手天下知 > 第二百三十一章 大战开启新的时代到来(第2页)
第二百三十一章 大战开启新的时代到来(第2页)
>“昨日有人为陌生老人撑伞,记一笔善。”
>“西巷李家媳妇生了女儿,全村扫街三日以贺。”
“这是哪里?”苏念在梦中问他。
林北停下动作,回头看了她一眼,微笑道:“这是未来的世界。只要你还愿意扫,它就会存在。”
醒来时,天还未亮。
苏念披衣起身,走到甲板上。晓尘已在那儿,手中捧着一本破旧的册子,正在默读。那是《归尘手札》第一卷,据说是赵擎亲笔所著,记录了最初十年间三百六十五位志愿者的日志摘录。
“你知道吗?”晓尘忽然开口,“赵擎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别叫我创始人,我只是第一个弯腰的人。’”
苏念点头。
“他还说,真正的归尘运动,永远不会出现在新闻头条上。它只会发生在某个凌晨四点的菜市场,一个摊主默默帮残疾邻居收摊;发生在暴雨中的十字路口,高中生脱下校服盖住井盖上的积水警示牌;发生在医院走廊,护士长悄悄把一份匿名捐款塞进贫困家属的背包里。”
“这些事,没人会报道。”苏念轻声道。
“但有人会记得。”晓尘合上书,“而且,总有一天,它们会连成一片光。”
船抵南方港口那天,阳光正好。
码头上站着一群人,有归尘学堂的孩子、老渔民、退休教师,还有几位曾参与早期重建工作的志愿者。他们没有横幅,没有锣鼓,只是静静地举着扫帚,排成两列,从岸边一直延伸到公路入口。
这是归尘最高的礼遇??以扫帚迎归人。
苏念、晓尘、陈素芬三人并肩走下舷梯,踏上陆地的一瞬,两侧同时响起整齐的扫地声:
沙……沙……沙……
那声音汇成一道河流,冲刷着旅人一路带来的疲惫与风霜。
当天下午,苏念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电话那头是个年轻女孩,声音颤抖:“苏老师……我是林小雨。我在西部高原接到通知,说您回来了。我想请您去一趟归尘大学。”
“什么事?”苏念问。
“有个学生,等了您三个月。”女孩顿了顿,“他说,他是林北的儿子。”
苏念的手猛地一颤。
“他叫林昭,十六岁,去年徒步两千公里来到高原,只为入学。他不肯接受特殊照顾,坚持和其他人一样背石头、挑水、扫雪。他说……他说他父亲从未教过他武功,也没留下一句话,但他记得一件事??每天早上,家里门前的台阶都会被扫得干干净净。”
苏念沉默许久,最终只说了一个字:“好。”
一周后,她抵达归尘大学。
校园建在海拔三千米的台地上,四周群山环绕,天空湛蓝如洗。没有教学楼,只有分散在草原上的数十座毡房与木屋;没有铃声,取而代之的是清晨传来的扫帚声与诵读声交织而成的“课号”。
林昭是个瘦高的少年,皮肤被高原阳光晒得黝黑,眼神却异常明亮。他见到苏念时并未跪拜,也没有哭泣,只是深深鞠了一躬,然后从怀中取出一块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把磨损严重的竹帚柄,末端刻着两个模糊的小字:“念安”。
苏念的眼泪瞬间落下。
那是她小时候的名字。母亲曾在日记里写过:“愿吾女苏念安,一生平安。”
“父亲留下的东西很少,”林昭低声说,“但这把扫帚,他一直挂在床头。他说,这是他欠这个世界的一句道歉。”
“道歉?”苏念哽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