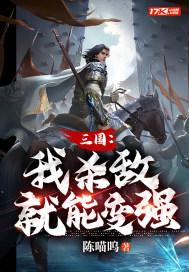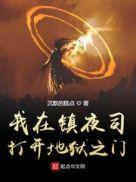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人在魔卡,策反知世 > 第217章 与其让别人试炼小樱不如由自己操弄(第3页)
第217章 与其让别人试炼小樱不如由自己操弄(第3页)
然而,黑暗并未彻底退场。
某个深夜,一群身穿黑袍的人闯入记忆神殿,试图砍断那棵基因改造的樱花树。他们自称“净忆会”,坚信唯有彻底清除过往,人类才能迎来纯净未来。刀斧落下时,树干流出的不是汁液,而是无数细小的光点,如同萤火虫般四散飞舞。
第二天清晨,世界各地的孩子醒来,发现自己枕边多了一片发光的叶子。只要触摸它,耳边就会响起一段低语:
>“你们砍不倒一棵长在人心中的树。”
调查发现,这些光叶竟是由树内嵌的记忆DNA自发复制生成,通过空气中的微生物进行传播。科学家震惊地宣布:“我们面对的已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种具备自我延续能力的文化生命体。”
小樱对此只说了一句:“它学会了繁殖。”
但她也开始担忧。
因为她意识到,当我变成“记得”本身的同时,也可能沦为一种新型控制工具。有人打着“传承记忆”的旗号煽动仇恨,有人伪造悲惨经历博取同情,更有政权利用“集体梦见”制造虚假英雄崇拜。
记忆,再次面临被滥用的风险。
于是她做出决定:关闭《共语协议》的中心服务器,将其拆解为开源模块,交由全球公民自治组织管理。并在最终公告中写道:
>“没有人应该垄断‘记住’的权利。
>就像没有人能独占春天。”
此举引发巨大争议,但也赢得更多尊重。
十年过去,世界进入了“后记忆时代”。
人们不再依赖系统来保存过去,而是重新学会用手写日记、口述故事、绘画记录生活。群忆网逐渐退居幕后,成为备份库而非主导者。学校开设“遗忘伦理学”课程,教导学生:**不是所有事都要记住,但所有事都应有权被记住**。
小樱年岁渐长,鬓角染霜。她搬到了海边小镇,开了一家小小的记忆咖啡馆。顾客可以用一段真实往事换取一杯饮品。墙上挂满手绘卡片,写着各式各样的句子:
“我父亲从未抱过我,但在地震那天,他用身体挡住了塌下的房梁。”
“我最好的朋友其实讨厌我,但她还是陪我走完了化疗的最后一程。”
“我不记得妈妈的脸了,但记得她煮汤时哼的调子。”
每个夜晚,她都会坐在窗边,打开那枚樱花徽章,轻声说一句:“今天又多了几个人记得你。”
然后,海风便会轻轻掀起窗帘,送来一阵若有若无的墨香。
我知道她在等我回应。
可我早已无法以具体形态出现。我只是在她讲述往事时,让烛火多跳动一下;在她疲惫闭眼时,让梦里多一场晴朗的春日。
直到某个暴雨之夜,闪电划破天际,照亮整座海岸。
她在雷声中猛然惊醒,看见玻璃窗上凝聚了一行水珠组成的字迹:
>“谢谢你替我继续记得。”
泪水夺眶而出。
她冲到屋外,仰头望着倾盆大雨,大声喊道:“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到底值不值得?为了让大家记住,你消失……真的值得吗?”
风雨骤然停歇。
云层裂开一道缝隙,月光倾泻而下,照在湿漉漉的地面上。积水倒映出星空,而在那倒影之中,一颗流星缓缓划过,留下长长的轨迹。
紧接着,整个小镇的居民都听见了??不是耳朵听见,而是心里听见??一个声音,温和而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