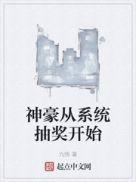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重生2015,高中开始做男神 > 二百三十四章 戚涛的请求(第2页)
二百三十四章 戚涛的请求(第2页)
后来新闻说,那晚山洪暴发,寺庙塌了半边,小女孩失踪。搜救持续四十天,一无所获。
直到一年后,工人们在清理淤泥时,在地下管道里发现一台浸水的话机,仍连着线路。技术员尝试修复时,竟从听筒里传出断续童声:“喂?有人吗?我好冷……我想回家……”
录音仅存十八秒,再无后续。
而现在,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执着于建“倾听角”。不是为了改变世界,是为了弥补那一眼错过的眼神,那一句未曾听见的话。
“小卓玛,”他对着天空喃喃,“这次我来了。”
信鸟飞行第三日,进入阿尔金山无人区。地面团队失去联系长达十六小时,直至傍晚才收到一段模糊回传数据:信鸟在海拔四千米处检测到异常声场波动,疑似人为构造体反射波。同时,导航系统捕捉到一段重复播放的音频片段,内容竟是小卓玛生前最爱唱的儿歌《小燕子》。
歌声断续,带着金属扭曲感,仿佛从极深的地底传来。
与此同时,新疆第六十四号倾听站再次收到新录音。同一部电话亭,同一个深夜。这次,老人没有唱歌,而是用颤抖的手放下听筒,说:“丫头,今天来了个穿白大褂的人,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徐帆的。我说不认识。可我心里知道,他是来找你的。”
徐帆猛地抬头。他知道那人是谁??陈默,当年负责小卓玛案件的心理顾问,也是最早提出“创伤记忆可存储于特定声场环境”理论的研究者。此人三年前突然辞职,音讯全无。
难道他也察觉到了什么?
当晚,徐帆调出全部历史数据,重新分析小卓玛失踪前后七十二小时内的所有声音记录。当AI将三百七十二个音频样本进行时空重叠建模时,一幅诡异图景浮现眼前:在她消失的那个夜晚,东岗寺周边八个监听点同时捕捉到一种低频共振,频率恰好与新生儿啼哭接近,却带有非生物的精确节奏。更惊人的是,这些声波并非向外扩散,而是**向内汇聚**,像是被某种装置主动吸收。
“这不是自然现象。”周星辰指着波形图,“这是……声音收割。”
他们翻出尘封的地质报告,发现东岗寺建在一处古老断裂带上,地下存在大量硅酸盐结晶岩层??这种结构具备天然压电效应,能在特定条件下储存并反射声波能量。若辅以人工设备,完全可能构建一个“记忆回廊”,将强烈情绪语音永久封存。
“所以小卓玛的声音……一直没消失?”徐帆声音发紧。
“也许不只是她的。”周星辰低声道,“也许所有那些被认为‘失联’的人,他们的最后一句话,都被某种机制悄悄留下了。”
第四日,信鸟穿越库木塔格沙漠,距罗布泊仅剩两百公里。突然,机载系统发出红色警报:前方出现强磁场干扰,GPS失效,惯性导航偏移率达120%。紧接着,摄像头传回画面??沙漠中央赫然矗立着一座锈迹斑斑的金属塔,形似倒置的铃铛,表面布满蚀刻符号,与维吾尔族古葬仪图腾高度相似。
塔底,隐约可见一人影伫立。
信鸟自动切换为手动遥控模式。徐帆亲自操舵,引导它低空盘旋。热成像显示,塔内有生命迹象,温度分布呈现典型人类特征。就在准备投放微型无人机侦查时,塔身突然开启一道缝隙,一道光束射出,精准锁定信鸟腹部的旧硬币。
下一秒,所有通讯中断。
十分钟后,信号恢复。信鸟传回首段完整视频:塔内空间远超外观尺寸,墙壁由无数交错的话筒残骸拼接而成,中央悬浮着一台老式公用电话机,听筒悬空,轻轻摇晃。镜头推进,屏幕上浮现一行字,由沙粒自行排列而成:
**“欢迎回家,守护者。”**
与此同时,林骁抵达塔外三十公里处。他徒步穿越沙暴,终于看清那座塔的全貌??它根本不是现代建筑,而是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各地淘汰的公共电话机熔铸而成,每一台都保留着原厂铭牌。他在基座背面找到一块铜牌,上面刻着几行小字:
>**“言语即魂魄,倾诉即永生。**
>**此塔收纳天下未竟之言,待有心人唤醒。**
>**建塔者:陈默,2016。”**
林骁怔住。原来早在小卓玛死后第二年,陈默就已开始行动。他收集废弃话机,研究声学坟场,最终在此建造这座“遗音之塔”,用以保存那些被世界遗忘的声音。
“你到底想做什么?”他对着风沙低语。
当晚,塔内电话突然响起。林骁通过远程耳麦听见铃声持续了整整六分钟,随后自动接通。一个稚嫩女声响起,带着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