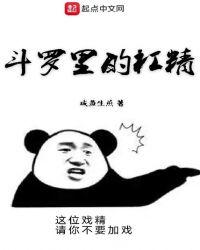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农野悍夫郎[种田] > 6070(第4页)
6070(第4页)
可是惹不得,裴松忙抽回手。
心说拎回家去,还不晓得它同豆饼谁更犟劲,到时后院儿定是好一番鸡飞狗跳。
土坑挖得差不离时,夜已沉得望不见远处的树影。
秦既白俯身用石斧把坑壁修得陡直,又将坑底敲得平整,免得猎物掉进来还能踩着土块爬出去。
待这些做好,还需插上刺桩。
汉子早早用猎刀削好了几根竹条,用火燎过后,每根竹条的顶端都尖若刀刺,十足锋利。
见汉子起身,裴松忙将坑口的竹刺递过去,怕伤到人,还注意将尖头的方向朝向自己。
秦既白伸手接过,又俯身探进坑底,先在角落踩出三个浅窝,将三根竹刺分别竖进去,再握住竿处往下压,直到竹刺稳稳扎进硬土,只留尺许长的尖刺朝上,刚好对着坑口方向。
裴松举着火把凑到近前,见汉子灰头土脸的免不了一阵心疼:“冷不冷?棉衣给你。”
秦既白仰头看他,暖黄火光映着男人的脸,他瞧见便踏实,酒意早随着热汗被风吹散,这会子确有些冷了,可他担心裴松受寒,只笑着道:“你穿着,我不碍事。”
天色昏暗,俩人又离得远,裴松摸不着人,只得点点头:“要不要再压点碎石?省得猎物把竹刺撞歪。”
秦既白应下声,接过男人递来的编筐,倒出石块子,顺着竹竿根部压实了。
他还特意将剩下的两根竹刺斜着插在坑壁下方,尖刺斜指坑心,就算猎物贴着坑壁往下滑,也躲不开这几道冷刺。
待几根竹刺都埋好,秦既白蹲在坑边打量,见尖刺错落分布,刚好能罩住坑底大半区域,这才直起身:“松哥,麻绳子帮我放下来。”
陷阱一人来深,再是强健的汉子也很难徒手上攀,好在麻绳子足够长,一端系在树桩下顺着土坑下放,拽紧了便能爬出去。
秦既白将绳子另一端系在腰间,一抬头就见裴松已朝他伸出手,他胸膛暖胀,借着绳子的拉力使劲儿一蹬,握紧男人的手猛然翻了出来。
一声闷响,秦既白扑了个满怀。
月光散了一地,一片冷凄凄的白,裴松将人搂紧了:“你小子可真沉。”
汉子脸色泛起红,急匆匆翻下去,忙又起身拉他:“撞疼没?”
裴松爬起来,伸手拍了拍土:“哥又不是面团捏的,没事儿。”
后续的活计便简单许多,竹子搭成稀疏的网格,再铺上层层叠叠厚实的叶片就是。
秦既白正去搬竹条,却被裴松按住肩膀,紧着棉衣裹在了他身上:“你歇着,后面哥来。”
“松哥我不累。”
他正想揭下棉衣,裴松的两只手却捧住了他的脸颊:“坐着去烤烤火,脸都冻僵了。”
火把快烧尽了,秦既白赶忙换了一把,野风劲起,火苗窜起半尺高,映得指尖一片暖光,他没坐下歇,凑近了给裴松打着亮堂。
两人合力干活儿,赶在后半夜将陷阱铺得平实,汉子又将余下的狐肉、白油撒在叶片上,这才同裴松回了住处。
夜色已经漫过山野,浑身疲累不堪,可裴松还是顶着困倦烧了热水,又怕风冷着人,给汉子端进里间去擦洗。
山穴地界够大,山野鸡被安置在角落,裴松给撒了把米,它正缩着颈子休憩,竟也没心思管这些吃食。
青石块儿将洞口堵紧实,月光却顺着缝隙泄进来,一地细碎的银。
真是累得紧了,汉子也不再闹着要做,缩在被里好生乖巧,他生得俊,闭目时侧脸如画中仙,不怪裴椿说他狐狸精。
裴松想起他才来家时候,重病不愈就睡在他房里,另搭的一张床板子,他时常这样安静无声。
在啥时候变了,该是成亲后吧,按杏儿的话儿便是“可叫他给赘进来了”,他知晓自己再不会不要他,越发赖人。
可他却欢喜,好生欢喜。
床铺太小,俩人抱紧了睡,挨贴得密实,裴松搂住人,在汉子额头上亲了亲:“后半夜了,不守了,好好睡。”
秦既白明明高裴松许多,却偏爱躬着身窝在他颈间、胸膛,手臂抱紧了轻轻地蹭:“松哥、松哥……”
“在呢在呢。”将被子掖好,裴松温声道,“臭小子。”
*
石尖在穴壁上又刻下一记,俩人进山已半月,明儿个就是汉子的生辰了。
算下此间打到的猎物,山野鸡一只,赤狐皮一条、灰兔皮两条。
野鸡暂且留下不卖,两条兔皮估摸三百来文,狐皮价高许多,只可惜不是玄狐或雪狐,这两样毛色若是上乘,能卖过三两,他这条赤褐色的,回去尽心硝制,该有一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