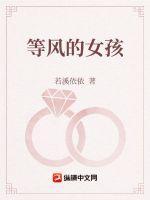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掌门怀孕,关我一个杂役什么事 > 第475章 以前都是你保护我现在换我来保护你吧(第3页)
第475章 以前都是你保护我现在换我来保护你吧(第3页)
台下掌声雷动。
就在此时,会场灯光忽暗。
大屏幕闪出一行字:
>**你说不出口的,我会替你说。**
紧接着,一段音频缓缓播放??是十年前,南极科考船上那位年轻助理撕开头环后的嘶吼:“够了!我们不是清除语言,我们是在杀死记忆本身!”
全场哗然。
随后,更多声音接连响起:
-东京聋哑学校老师第一次听见手语颜色时的哭泣;
-巴黎研究员念出阿呜氏遗言后,钢笔飞舞划出金线的嗡鸣;
-非洲裂谷石棺开启时,大地震动的低频轰响……
每一段都精准对应沈知白人生中的某个抉择时刻。这些录音本已销毁,却被语核母体从集体潜意识中重新提取。
沈知白脸色惨白,踉跄后退。
突然,他的耳机自动启动,传出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老师,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林昭阳最后一个学生。那时候,你说我写的诗太疯,让我吃药。可我还是写了,每天半夜躲在厕所里,用卫生纸记下梦里的话。后来你把我送进了疗养院,说我是‘语言妄想症患者’。”
声音停顿一秒。
“现在,我想告诉你??那首诗,我一直记得。”
接着,一首极轻极缓的童谣响起:
>“月亮不吃米饭,
>它只喝露水。
>哥哥不说话,
>因为他怕惊醒星星。”
沈知白浑身剧颤,双手抱头,指甲深深掐进太阳穴。
“不……这不是真的……我没有……”
“你有的。”青年的声音穿透音响,“你记得这首诗。因为你女儿也写过类似的。但她发烧那晚,你亲手烧了她的笔记本,说‘别让孩子学坏’。”
全场死寂。
沈知白猛然抬头,眼中第一次浮现出剧烈的情感波动??不是愤怒,不是恐惧,而是**悔恨**。
“我……我只是想保护她……让她活得轻松一点……”
“可她后来再也不肯画画了,对吗?”青年的声音柔和下来,“她十八岁那年跳海了。临走前,在沙滩上写了三个字:‘我想说。’”
沈知白跪倒在地,无声痛哭。
那一刻,整个会场的人都听见了??不只是声音,更是三十年来被他自己亲手埋葬的父爱。
有人开始流泪,有人低头私语,还有人当场撕毁了手中的“语言规范手册”。
会议被迫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