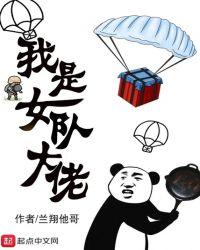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强取豪夺了黑月光 > 4045(第2页)
4045(第2页)
但这可是宋瓒,纯血的封建大爹,绝对的阶级分化拥护者。
容显资有些拿不准。
见容显资还是不说话,宋瓒心里有些空落落的,却不知道该做何,便回了案上办公。
昨夜那迷药的劲还有些残留,容显资也躺得舒服,顺便缓缓这药劲。
这紫檀木软榻高矮十分合适,铺着的退红锦锻软垫,杏仁黄的引枕抱枕一应俱全,还有一条轻巧羊绒毯子。
虽然金贵用心,但在这庄严肃穆的书房显得格外格格不入。
只怕是宋瓒命人另外安排的。
容显资摸了摸这紫檀木,估摸着怕是三月前就打好了。
也就是八月,还在成都府的时候。
八月十五中秋前一日同宋瓒撕破脸,宋瓒又在冬月十五摆了她这一道。
这衔尾蛇玉镯子,这紫檀木软榻,还有许多明显与宋瓒院子方枘圆凿的东西,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置办好的。
那宋瓒也必是做了万全准备把她接到这院子的。
房内二人各怀心思都不言语,宋瓒没有唤人进来研墨,只蘸着方才容显资磨的那点子墨。一刻钟后,那墨便见了底。
宋瓒看着砚台,又看向容显资背影,嗫嚅开口:“你若是想打麻将,我不在院内陪着你时,叫她二人来罢。”
他皱皱眉,又补道:“再唤上你那婢子。”
闻言容显资起身,淡淡扫过他:“宋婉现在是你妹妹。”
见容显资终于肯开口,宋瓒那压着的石头松开些许:“你应该知道,我是因为你才留那婢子一命,否则我有千万种办法杀了她。”
“你既不愿同季夫人亲近,何必阻止她有个贴心的女儿呢?”容显资叹气。
宋瓒凝眉,有些茫然:“她为什么要有一个贴心的女儿?”
容显资被这反问哽住,可见宋瓒的神色,他似乎确实不明白季筝言为什么需要一个贴心的儿女。
她突然想到宋瓒总是挂在嘴边的“管束”。
那是谁管束的宋瓒?竟叫他完全摒弃了母亲。
眼下纠结不出此事,容显资转过话题:“你准备锁我多久?”
她将脚上的金锁链一甩,弄出声响。
“不急,我不拘着你,你可以下床走动,待你学乖一些了,也可离院。”宋瓒笑着开口,那语气好像他多么宽宏大量一样。
容显资深吸一口气,试着和他周旋:“你这金锁链便约莫十斤重,又限制了我步子,我为何出不得院子?”
宋瓒欣赏着她气急败坏的模样:“你太狡猾了,而且没有内力都能和我过招,总得多防着。”
他走上前嗅嗅容显资的香味:“而且,你身上野性太重,总得先洗干净了,再去接受教化。”
容显资表情平静看着宋瓒,最后缓缓吐出两个字:“有病。”。
此后几日,果然如宋瓒所言一般,容显资的脚链就没有松开过,被绑着十斤重的东西,容显资也懒得动弹了。
她也尝试过套丫鬟的话,但丫鬟除了应下伺候她的回话外,基本不敢同她多言一句。
同时她逐渐明白宋瓒为什么这般瞧季玹舟不起了,此朝商人低贱,与此相对应的,便是官宦的绝对高位。
所以季玹舟身边的仆从,同容显资在现代家里的阿姨司机感觉大差不离。
但宋瓒这里的仆从,就是完全的卑从和屈服了,是连下人自己都认为,从人格上她们比宋瓒更低贱。
这是一件让容显资万分不适的事情。在现代,虽然因为运气,出生等多方位因素,总有人社会地位会更高。这群人里面也会有脑残觉得自己比别人更高贵,但总归很少有人主动觉得自己比别人更低贱的。
常言道宰相门前七品官,宋瓒院里的下人,又将这一套阶级链施加给了平常百姓家里的佣人。
在这套观念下,并没有发生容显资以为的,会有人来劝自己珍惜或者知足的情况,因为说这种话的前提是劝诫的人会推己及人,而宋瓒院里的人并没有认为她们有和容显资相提并论的资格。
因为她们认为容显资是主子,主子做事下人是连想的资格都没有的。
她没打算同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做斗争,但也不觉得自己有那个坚定的意志去反抗这种人上人的爽感。
所以久而久之,容显资也尽量避免同她们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