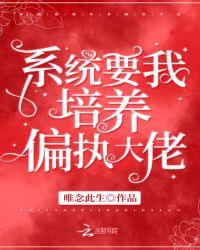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娱乐圈的老实人 > 第165章 一场游戏23求月票(第1页)
第165章 一场游戏23求月票(第1页)
很快,就轮到了这场重头戏。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
古色古香的大殿之中,眼下已经被布置了一道道屏风。
这里本来是后宫戏拍摄常用的场景,有好几部唐宫剧的华清池就是在这间宫殿里面取景的。。。
雨后的空气里浮着泥土与青草的气息,张鸿沿着老城区的石板路缓缓走着。他的脚步不急,仿佛怕惊扰了这座城刚刚苏醒的宁静。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几下,他没立刻拿出来看??他知道,那不是紧急消息,而是平台后台推送的日常提醒:又有三份来自偏远地区的作品完成了区块链存证;一位内蒙古牧民上传了用蒙文写下的草原传说合集;贵州山区的一位支教老师组织学生集体创作了一部名为《星星掉进山洞那天》的童话集。
这些名字、这些声音,正像春藤攀援般,一寸寸爬上原本荒芜的认知高墙。
他拐进一条窄巷,在尽头的小店前停下。这是家开了二十多年的老式照相馆,招牌上的漆已斑驳脱落,“光明影像”四个字歪斜地挂着,玻璃橱窗里摆着泛黄的全家福和穿白衬衫戴红领巾的学生照。推门进去时,风铃轻响。
柜台后坐着个中年男人,戴着老花镜,正低头修一张底片。听见动静抬起头,愣了一下:“张老师?”
“老周。”张鸿笑了笑,“还记得我。”
周建国是江城最早一批街头摄影师,九十年代拍过无数工人家庭的生活剪影。后来数码时代来了,相机更新换代,他的手艺却没人学,生意一年不如一年。三年前,他在平台上上传了一组题为《最后的胶卷》的照片:破败的纺织厂门口,女工们抱着孩子站在夕阳下,眼神空茫又坚韧。那组照片被林晚秋看到后推荐给了某文学期刊,成了配图专题,还引发了关于“城市记忆断层”的讨论。
“你怎么来了?”周建国摘下眼镜,语气里带着点不敢信的激动。
“来看看你。”张鸿从包里拿出一台翻新的胶片相机,“这是我在旧货市场淘到的禄来双反,成色不错,镜头也没霉。我想……也许你能用它继续拍下去。”
周建国的手微微发抖,接过相机,指尖轻轻抚过机身上的划痕。“这机器……跟我年轻时用的那一台,几乎一模一样。”
“不只是相机。”张鸿说,“是我们得让那些快要被人忘记的脸,再被看见一次。”
周建国沉默良久,忽然转身从柜子里抽出一个牛皮纸袋:“我一直在拍。没停过。只是不知道往哪儿寄,也不知道谁会看。”他打开袋子,里面是一叠冲洗好的照片??凌晨四点的菜市场,卖豆腐的老夫妇并肩坐在小凳上打盹;桥洞下蜷缩着的流浪歌手抱着吉他睡着了,怀里还夹着未写完的歌词;还有个七八岁的女孩蹲在公交站牌前,用粉笔在地上画一座城堡,旁边写着:“我家在这里。”
“这些都是‘等光的人’。”周建国低声说,“他们不说话,也不争,可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叙述。”
张鸿一张张看着,喉咙渐渐发紧。他忽然明白,为什么当初自己会在那栋废弃居民楼里捡到装着手稿的铁盒??因为这座城市从未真正沉默,只是太多人的声音被时代的喧嚣盖住了。
“我要办个展览。”他说,“就叫《未命名者日记》。全部免费开放,地点就在新落成的‘流浪故事收容站’一楼展厅。你来做主展摄影师,所有作品由平台出资印制,并附上口述文字和存证编号。”
周建国怔住:“真的可以吗?这种……没人知道的名字,也能办展览?”
“正因为没人知道,才更该被展出。”张鸿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我们不是在寻找天才,是在找回被忽略的真实。”
三天后,施工队进驻收容站,开始搭建临时展架。与此同时,平台发起众筹活动:“为一百个普通人举办人生第一次展览”。响应者远超预期??七十二小时内,收到两万三千多份投稿申请,涵盖摄影、手绘、日记本、手工模型甚至一段段手机录下的方言童谣。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一位聋哑老人寄来的陶艺作品。她住在皖南山村,靠种茶为生,儿子早年外出打工失联。她在平台上提交了十件陶器照片,每一件都刻着不同的符号:月亮、翅膀、门、船、信封……鬼鬼联系当地志愿者上门探访,才发现那些符号,是她为失散儿子创造的“语言”。
“她不会写字,也不识字。”志愿者在回传视频里哽咽道,“但她相信,只要把这些东西烧进泥土里,总有一天,她的孩子会摸到它们,读懂她想说的话。”
张鸿当即决定,将这件作品列为展览核心展品之一,并邀请中国美术学院的团队协助建立一套可视化的“情感编码系统”,尝试将这位母亲的语言转化为公共可读的艺术表达。
筹备期间,林晚秋也回来了。
她不再是那个躲在出租屋里反复修改手稿、害怕被人认出的作家,而是一个眼神坚定、步伐沉稳的女人。她带来了新的计划:以《月亮熊》为基础,联合心理学专家和儿童公益组织,开发一套“叙事疗愈课程”,专门用于帮助经历重大创伤的孩子通过写作重建内心秩序。
“我不再只想写故事。”她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我想让故事成为药。”
项目启动当天,第一堂课在福利院举行。十几个孩子围坐成圈,有的怯生生低着头,有的咬着铅笔不肯动笔。林晚秋没有讲技巧,只是轻轻翻开小芸写的《小芸篇》,读起那段关于“会唱歌的药丸”的故事。
有个小女孩突然举手:“姐姐,我也想写,可是……我忘了妈妈长什么样了。”
教室一下子安静下来。
林晚秋蹲下身,握住她的手:“那就从‘我记得一点点’开始写。比如,她煮的粥是不是特别烫?她哄你睡觉时会不会哼跑调的歌?哪怕只记得一缕味道、一声咳嗽,都是真实的。”
孩子眨了眨眼,终于拿起笔,在纸上写下第一句:
>“我的妈妈喜欢穿蓝色的裙子,风吹起来的时候,像湖水荡漾。”
那一刻,张鸿站在教室后方,感觉心脏被什么狠狠撞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