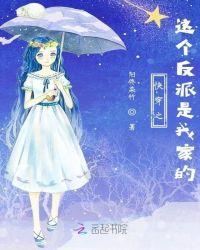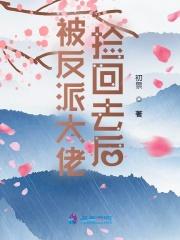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稚御山河 > 第五十四回 万民伞里藏讥刺 午朝殿上问初心(第3页)
第五十四回 万民伞里藏讥刺 午朝殿上问初心(第3页)
张贵祥见状,知非同小可,不敢耽搁,连忙回身入明章宫,将情由一五一十奏明皇帝。皇帝放下玉箸,眉头微蹙,望着殿外沉吟:“早朝刚退,怎么又要开午朝?有什么事明日不能说吗?”
张贵祥躬身道:“陛下,看齐王这架势,情非得已,是非开午朝不可。”
皇帝看了看桌上未毕的膳食,叹了口气,一脸委屈:“可朕的膳食还没用完呢……这皇帝当的真没意思。你告诉齐王,能不能让他明天再来?”
张贵祥见状,只得应下,转身出了宫门,对齐王把皇帝的话一五一十说了。
齐王仍长跪不起,沉声回道:“今日陛下若不开午朝,臣宁愿跪等。”
张贵祥刚要回身入殿回禀,宫门外,齐王忽地昂首朗声道:
“祖训有云:‘君者,万民之主也;朝者,治世之纲也。’凡遇吏治昏浊、民心动荡,或有重大疑案未决,当不拘早午,即时开朝,以正视听、以安天下。‘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苟害黎民,寝食难安。’今城阳一案,牵系官德、关乎民望,非午朝当面定夺,不足以服众,不足以慰苍生!”
字字铿锵,掷地有声,穿透宫门,直入明章殿内。
皇帝刚端起茶盏,闻言一愣,蹙眉道:“他念的是什么?”
张贵祥连忙躬身:“回陛下,是祖训要义。齐王言明,若陛下今日不开午朝,他便要去敲登闻鼓——此鼓一开,便是‘民情直达天听’,按祖制,陛下即便不愿,也需临朝受诉,届时百官齐聚,天下皆知,反倒更难收场。”
“真有此事?”皇帝将信将疑,放下茶盏,脸上仍带着几分不耐,“不过是一桩地方旧案,值得这般兴师动众?”
他沉吟片刻,望着殿外那道跪着的身影,终究松了口,却仍带着几分委屈:“罢了,让他跪着吧。传旨,即刻备午朝,百官入承光殿议事——朕这顿饭,算是吃不成了。”
张贵祥连忙应声:“遵旨!”转身快步出殿,对齐王高声道:“王爷,陛下准奏,即刻开午朝,请王爷起身,随臣入殿候驾!”
齐王闻言,缓缓叩首谢恩,额头再次触地,声音带着一丝释然:“谢陛下!”
说罢,他撑着地面起身,冠服虽沾了尘土,脊背却依旧挺得笔直,随张贵祥大步迈入明章宫,往承光殿而去。
承光殿内,文武百官鱼贯而入,阶前肃立。丞相孙幽古出班,目光沉静:“自陛下登基以来,并无午朝之例,何故今日仓促召集?”
齐王出班,躬身一礼:“扰了各位大臣的清暇,也搅了诸位的家事,本王在此谢罪。今日恳陛下开午朝,实非无因。”
一位大臣忍不住问道:“齐王请午朝,究竟为哪般?”
齐王抬眸,语气一沉:“为明是非、正吏治、安民心。此事牵系城阳积弊未清,更关乎朝堂纪纲,不可不开。”
他目光一转:“桂宁侯王世烈在吗?”
桂宁侯出班:“在。”
“侯爷在就好。”齐王颔首,“诸位大臣,本王开午朝并非无的放矢。城阳一案,供词虽定,人心未服;万民伞诗文虽美,民谣却怨;杜之贵之罪,不止一端。若不趁此时当面定夺,恐生枝节,动摇社稷。”
他顿了顿,声音更重:“今日请午朝,一是奏请陛下准大理寺、御史台、刑部三司会审,彻查城阳三年来漕渠、税赋、赈灾诸项;二是请将张翠喜案与杜之贵、周启元案并案复核,厘清牵连与构陷;三是请颁旨约束内外臣工,凡涉地方兴作,必以民意为先、以法度为准。”
“此事重大,非早朝仓促可议,亦非明日可缓。”齐王再拜,“臣请陛下准此三事,今日当面裁决。”
阶下百官神色各异。孙幽古沉吟片刻:“若真如齐王所言,此事确需早定。臣请陛下准三司会审,其余二事,容百官再议。”
桂宁侯脸色微沉,按捺未言。钱尚书站在班中,指尖微紧。
皇帝在御座上目光流转,见百官肃立、齐王持重,终于颔首:“既如此,准齐王所请。三司即刻会审,其余二事,百官各抒己见,今日一并议决。”
“谢陛下!”齐王再拜。
承光殿内,议论之声渐起,午朝就此开议。
齐王出班奏道:“请陛下传杜之贵。”
皇帝道:“那就传杜之贵吧。”
杜之贵至承光殿,扑通一跪:“罪臣拜见陛下!罪臣拜见陛下!”
皇帝道:“齐王,你可以发问了。”
齐王上前一步,沉声道:“杜之贵,你在大理寺言之凿凿,称自己在城阳三年‘有功无过’。本王且问你——你当真有功无过?”
他抬手,将一纸供词掷在杜之贵面前:“你这字据,桩桩件件颇有疑点。供词虽画押,却多有避重就轻、含糊其辞之处,不足为凭。”
又道:“你既已赴任扬州,那好——你在城阳任太守不过三年,如何能骤升扬州刺史?扬州刺史乃一方要员,秩在三品,关乎漕运军政、财赋民生,非寻常迁转可比。你一个四品下的官,凭何短短三年便能越级而上?你且道出,这升迁的缘由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