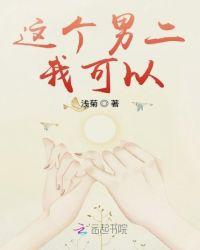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解春衫 > 第145章 再也回不去了(第1页)
第145章 再也回不去了(第1页)
几人沿着坡路走去,终于,在天完全暗下来前,看到前方有一小屋,不必进去,也知道是个无人居住的弃屋。
长安将木门推开,门板发出“吱呀”的晃动,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又走出来。
“废弃的,想是山里人搬走了。”
戴缨随陆铭章进到屋里,就着昏暗的光线,往这方破败枯朽的木屋打量。
有桌,有椅,桌椅的面上、横衬上覆了薄薄的灰,墙面的窗扇歪挂着,窗边搭了一块看不清颜色的布。
护卫拢了些角落的干草,堆在屋中,又将几个椅凳。。。。。。
夜色如墨,春衫书院的灯火却亮得如同白昼。新立的“明德堂”檐角挑着六盏琉璃风灯,在晚风中轻轻摇曳,映得门前青石板泛起微光。戴缨站在廊下,指尖抚过新版《春衫纪事》清样的封面,那三个字是她亲手所题,笔锋凌厉而沉稳,一如她此刻的心境。
可她知道,这光明背后,仍有暗流涌动。
归雁悄然走近,手中捧着一封密信,封口火漆未干,印着刑部特使专用的双鹤衔剑纹。“裴大人连夜派人送来的。”她低声说,“说是京中局势有变,谢府虽已查封,但宫中有人压下了‘换婴案’的奏本,圣上只准查‘人口贩卖’与‘勾结外邦’两项,其余一概留中不发。”
戴缨接过信,拆开细读,眉心渐渐锁紧。果然,皇帝对“公主身份”一事讳莫如深,仿佛那不是一场惊天阴谋,而是一桩不可触碰的禁忌。更令人心寒的是,原本支持女子科考的几位阁老突然改口,称“妇人干政,易乱纲常”,竟提议将国立女子学院纳入礼部监管,由宗妇主持教务。
“他们要夺走我们的魂。”戴缨冷笑一声,将信纸投入烛火,“今日让我们读书,明日便让我们跪着绣花。所谓恩典,不过是驯化的开始。”
归雁忧心忡忡:“先生,若朝廷真派宗妇入驻,学生必不服管束,届时冲突一起,反倒给了他们取缔的理由。”
“所以,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动手前,把根扎进地底。”戴缨转身步入藏书阁,取出一本薄册??正是《镜录簿》的副册,记录着散落各地的春衫分支学堂联络方式。“你立刻传令:南方七省识字班即日起转为‘隐学’,白日务农做工,夜间聚众授业;北方三路则以医馆、绣坊为掩护,继续收容逃婚女子。所有课程不得再用‘春衫’之名,改为‘织雪’‘听澜’‘照影’等代号。”
归雁点头记下,又问:“那林素心呢?她刚回来,身子还未养好,却执意要去塞外重走一趟商路,说是要救更多被拐的女孩。”
戴缨沉默片刻,望向窗外月色下的讲坛。那里曾是她第一次讲课的地方,如今已被青砖高台取代,雕梁画栋,气势恢宏。可她记得,当初第一个敢举手提问的女孩,叫柳二丫??父亲嫌她吃闲饭,九岁就许给了屠户做童养媳,是她半夜翻墙逃出,徒步百里来求学。
“让她去。”戴缨终于开口,“但不能再孤身犯险。派两名寻踪司老手随行,另调陈砚在幽州的眼线接应。记住,不求多救一人,只求不留一个活口证据。我们要让每一份罪恶,都变成钉在他们棺材上的铁钉。”
归雁领命而去。
翌日清晨,书院举行升格后的首次大课。戴缨登台讲授《女诫辨伪》,台下坐满三百余名新生,还有数十位闻讯赶来的士绅家眷。她不疾不徐,逐条批驳班昭原文中“卑弱下人”“夫为天”的荒谬,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连坐在后排的一位老儒都频频颔首。
讲至中途,忽有宦官携旨而来,宣读一道新谕:皇帝感念女子向学之心,特赐“贞静匾”一方,悬于明德堂正中,并命每月初一,全体师生须诵读《列女传》一个时辰,以正心性。
全场哗然。
戴缨缓步上前接旨,面上恭敬,心中冷笑。这哪是嘉奖?分明是精神枷锁!一块匾额,一句“贞静”,就想抹杀她们挺直脊梁的权利。
她当众跪接圣旨,起身时却朗声道:“臣女戴缨谨谢天恩。然《列女传》中有‘孟母断机’‘陶母退鱼’,皆赞女子明理持节、教子成才。今我书院所求,亦不过如此??非争权夺利,唯愿天下女子皆能识字明理,不负此生为人。”
言罢,她转向众人:“从今日起,《列女传》列为选修,每周讲习一次,由学生自择章节研读。若有疑问,可与《春秋》《孟子》对照参详,写出心得交予师长评阅。”
此举既遵了旨意,又守住了底线。台下掌声雷动。
然而风波未平,三日后,京城再传消息:谢景和在狱中暴毙,死状蹊跷,颈骨断裂,似被人徒手掐死。牢卒称当晚无外人进出,лишь御前太监送来一碗参汤,饮后不久便气绝。
戴缨闻讯,握杯的手微微发颤。
“李德全还没抓到。”她喃喃道,“而谢景和死了……死得太干净了。”
她太了解宫廷手段。真正的主谋从不会亲自沾血,只会让刀自己折断。谢景和不过是替罪羊,真正的黑手仍在幕后窥视,等着看她是否因愤怒失措,贸然上书逼宫。
“不能冲动。”她对自己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复仇,而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