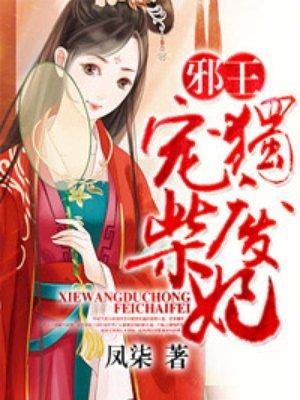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霹雳]如何在苦境变成人 > 第36章(第5页)
第36章(第5页)
跨过镜面的感觉,像是穿过了一层极冷的雾气,又像是从一个喧闹的房间,一步踏入真空,外界的、内心的、所有细微的杂音,在那一瞬间被抽离得一干二净。
金少爷发现自己站在一片……空之中。
不是黑,也不是白,而一种均匀的灰,像画布的底色,绵延至视线的尽头。
空气是静止的,没有温度,没有气味,也没有丝毫流动,他听不到呼吸声,心跳,仿佛他已成一座矗立在这绝对寂静的石像。
唯一的存在,除了自己,就是远处,静静站立的身影。
是另一个金少爷,或者说疏离者。
但他看起来……不同,身影模糊透明,仿佛由冰雕刻而成,反射着灰色的微光,他站得笔直,却有种轻薄感,仿佛下一刻就消散在灰色里,脚下没有影子,或者他本身便是一个影子。
金少爷想说话,却发现声音无法发出,不是禁止,而是空间拒绝任何形式的交流,任何声音都被吞噬。
他尝试向前靠近,但一股力量开始显现,不是排斥,而隔绝,像是一层不断增厚的坚冰,靠近一分,冰便厚一分。
疏离者始终没有回头,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对外界,包括另一个自己的靠近都无反应,或说是:我无需你,我即完整,我即孤岛。
金少爷在艰难前行距离十步时停下,不是无法靠近,而感觉,继续靠近,自己也将被同化成这片灰色寂静的一部分,失去自己的温度。
他第一次如此清晰感受到孤独的力量,不是被迫的孤单,而是一种筑起高墙,焊死大门,把自己与全世界甚至自己彻底隔绝的意志。
他想起来迷宫里,离所有人远点的低语,原来当这种念头占主导,构建出来的世界是这样,因无物,却也死寂。
他该这么做?像暴怒一样,运用力量?还是像戏谑一样,寻找真实?但似乎都不管用。
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只有一片凝固的永恒。
金少爷站在哪儿,最初的不适与焦躁,渐渐被无边的静平息,他开始感觉疲惫的平静,一种就这样吧的感觉袭上心头,或许他是对的,外面太吵,太痛,太复杂,留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不好。
他几乎要化作另一尊冰雕,与远处那个透明模糊的疏离者镜像,一同沉入永恒的静寂。
但,就在意识即将彻底冻融入这片绝对安全的虚无的前一瞬——
一丝异样,如同冰层下最微弱的潜流,触动了他几乎停滞的神经。
不是声音,不是景象。
是……感觉。
一种存在的感觉,并非来自他正在僵化的躯壳,而是来自……他脚下那片开始变淡、却依旧顽强连接着他的影子。
影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
是物理的移动,而是某种情绪的震颤,极其微弱,却带着与这片死寂灰色格格不入的温度。
那温度很复杂。有戏谑者领域对虚假快乐的厌倦与愤怒;有暴怒者领域自我毁灭后的痛苦与顿悟;有进入这疏离领域前,那些嘈杂低语带来的烦躁与抗拒;甚至……还有更久远,更模糊的,幼时流浪途中,偶然接过陌生人半块干粮时指尖的温热;第一次握紧抢来的刀时,掌心硌人的粗糙与心跳如鼓的悸动。
这些感觉,混乱、矛盾、带着刺人的棱角,绝不舒服,甚至大多痛苦,但它们真实。真实得灼热,真实得尖锐,真实得……与他相关。
这片灰色的绝对孤寂,试图抹去一切差异、一切连接、一切噪音,但它抹不去影子,影子是他走过的路,是他经历的事,是他感受过的所有温度,无论那是冰冷的刀刃还是短暂的火光,所沉淀下的黑暗证明。
金少爷那近乎冻结的思维,被影子深处这一点点混乱而真实的温度灼了一下。
他极其缓慢地,仿佛生锈的机器般,低下头。
脚下的影子,在均匀的灰色背景下,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黑,也更……沉重,它不再仅仅是一片平面,更像是一口深井,里面沉淀着他所有不愿面对,却又无法抛弃的杂质。
疏离者要他变成纯净的冰,透明的灰。但他……本来就是一团掺杂着污泥、热血、怒火、虚妄、迷茫的混沌,这混沌让他痛苦,却也让他活着。
他重新抬起头,看向远处那个仿佛与灰色融为一体的疏离者镜像,第一次,他不再试图靠近或对抗,而是开始理解那种姿态下的……空洞。
一个念头,如同破冰的春芽,艰难却执拗地顶开意识的冻土:
我不要变成那样。
我不要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