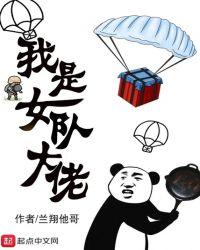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凌总,你的小祖宗回不来了 > 第345章 长夜已尽噩梦远离(第3页)
第345章 长夜已尽噩梦远离(第3页)
chapter_();
但他却放缓了节奏,带着无尽的怜惜和安抚。
慢慢亲吻着怀里的人儿。
自丁浅回来,自她回来,他们的世界就彻底坍缩了。
坍缩成只有彼此呼吸、体温、心跳交缠的方寸之地。
窗帘恒久垂落,隔绝日月。
时间沦为窗外光影毫无意义的明暗交替,再无人关心晨昏几何,日月轮转。
生活简化到只剩几个滚烫的、不断循环的动词:
亲吻。
。
喘息。
相拥而眠。
只要意识清醒,身体便像拥有独立的意志,饥渴地、急迫地寻求着对方的联结。
用滚烫的肌肤相亲,用濡湿的汗水交融,用失控的喘息和颤抖,固执地、一遍遍地在彼此身上刻下最原始的印记:
活着。
拥有。
永不分离。
语言成了最多余的东西,只在情动至极的间隙,破碎地滑落:
“凌寒……”
“我在。”
“别走……”
“死也不走。”
那句本该在重逢第一天就问出口的“你这些天,过得怎么样?”
早已被淹没在更汹涌的、需要用身体确认的洪流里,无人提起,也无暇提起。
变化的起点,是那个昏暗的黄昏。
丁浅靠在他怀里看窗外,忽然轻声说:
“少爷,我做了很多梦。”
凌寒正在给她揉捏有些酸软的腰肢,动作顿住。
“有些梦特别黑,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像被活埋在地底,喘不过气。”
“有些梦里有你。”
“有光,有声音,有你叫我‘浅浅’。”
“可每次醒来,房间里只有蓝色。”
冰冷的,令人窒息的蓝色。
是她独自一人面对仪器、药物和内心战争时,睁开眼唯一能看到的颜色。
凌寒的心脏像被冰锥狠狠捅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