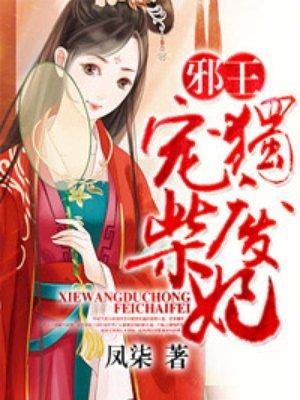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我在美利坚扮演众神 > 第167章 剩余的权能力量什么叫另外一半在天上(第2页)
第167章 剩余的权能力量什么叫另外一半在天上(第2页)
抵达学校时,礼堂已坐满了人。不止学生,还有几位母亲模样的妇女,甚至有两个穿着制服的社工。讲台简陋,只有一张桌子、一台投影仪和一盏落地灯。她走上前,没有打开PPT,也没有念稿。
“我想先放一段声音。”她说。
按下播放键,合唱团磁带的音频缓缓流出。十七个少女的歌声填满空间,纯净得不像属于这个时代。当唱到第三节那个变调的瞬间,全场安静了下来,仿佛空气都被抽走。
“你们听到那个声音了吗?”她问,“那个哽咽,或者说是笑?我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她的声音穿越了四十年,穿过磁带氧化、战争创伤、制度掩盖,最终在一个陌生女人的耳机里醒来。”
她停顿片刻,目光扫过每一张脸。
“这不是灵异事件。这是**情感的量子纠缠**??当你真心呼唤一个人的名字,哪怕相隔百年、万里,哪怕你们从未相识,那份思念仍可能触动某个频率,唤醒一段沉睡的记忆波。”
台下有人抹泪,有人低头记录,也有人微微颤抖。
“我们常听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她继续说,“可我想告诉你们,历史也是由失败者的眼泪浸透的。那些被删去的名字,被打断的故事,被定义为‘不重要’的痛苦,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潜入了集体意识的深海,等待某一天,被一阵风、一首歌、一句话重新掀起波澜。”
她拿出那本笔记本,翻开最新一页。
“过去我以为,我的任务是收集这些碎片,拼出完整的图景。但现在我知道,图景永远不会完整。有些人注定找不到墓碑,有些真相永远无法证实。可这不妨碍我们说一句:‘我承认你存在过。’”
她合上本子,轻声说:
>“承认,是最温柔的抵抗。”
讲座结束后,学生们围上来提问。有人问如何开始记录家族史,有人想知道怎样帮助朋友走出创伤,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女孩怯生生地举手:
“如果……如果我妈妈的名字已经被注销了,户籍上查不到,照片也都烧了,那我还能怎么记住她?”
谢峰成看着她,心口一紧。
“你可以给她一个新的名字。”她说,“不是替代,而是延续。比如叫她‘春天的第一缕风’,或者‘半夜给我盖被子的手’。你可以每天对她说话,哪怕只是说‘今天下雨了,你以前讨厌这种天气’。你可以在心里为她留一个位置,像留一盏不关的灯。”
女孩咬着嘴唇,眼泪滚落。
“记住不是占有,而是释放。”谢峰成走到她面前,轻轻握住她的手,“你不必背负她的痛苦,你只需要让她知道??她的存在,曾经点亮过这个世界的一角。”
活动结束已是傍晚。她婉拒了共进晚餐的邀请,独自走向地铁站。途中经过一家旧书店,橱窗里摆着一本泛黄的《日本殖民时期劳工档案索引》,价格标为“随缘”。她推门进去,店主是个华裔老太太,戴着老花镜,正在修补一本破损的族谱。
“这本书,”谢峰成指着橱窗,“我能看看吗?”
老太太取出来递给她。封面斑驳,内页纸张脆黄,但保存完好。翻到中间一页,她突然僵住。
上面列着一组编号与姓名,其中一条清晰写着:
>**金正浩,籍贯:朝鲜咸镜北道,派遣地:北海道煤矿,归国状态:未归,备注:疑似死亡,无遗体。**
旁边贴着一张小照片??正是她在札幌地下书市见过的那张合影中的男人,胸前别着铜牌。
她手指颤抖,几乎拿不住书。
“你知道这个人吗?”老太太忽然问。
“我……见过他的照片。”她艰难开口,“他还留下了信。”
老太太摘下眼镜,深深看了她一眼:“那是我舅舅。他妹妹,也就是我母亲,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哥哥,我对不起你,没能把你找回来。’”
谢峰成怔住。
“我们找了他六十年。”老太太低声说,“政府说他死了,档案说他失踪,连家乡的族谱都把他除名了。可我母亲每年清明都摆一双筷子,说:‘只要没人叫他的名字,他就还在路上。’”
谢峰成从包里取出那封未寄出的信复印件,双手递上。
老太太接过,读完第一句便泣不成声。
“谢谢你。”她哽咽道,“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听见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