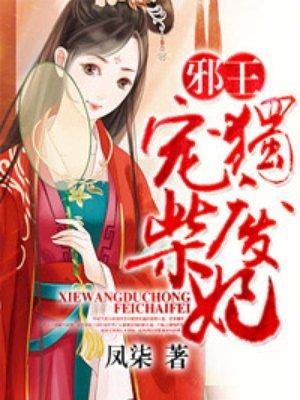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我在美利坚扮演众神 > 第167章 剩余的权能力量什么叫另外一半在天上(第3页)
第167章 剩余的权能力量什么叫另外一半在天上(第3页)
她们相对无言,唯有窗外车流如旧。
谢峰成离开书店时,天已全黑。她没有立即回家,而是走进附近一座小公园,在长椅上坐下。她掏出希望号,放在膝上,低声说:
“你听见了吗?他又被人叫了一次名字。”
布偶没有回应,但她感到它的心跳节奏变了,变得更稳,更像人类的脉搏。
她仰头望天。云层散开,露出几颗星星。她想起梅琳达曾说过:“每一个选择记住的人,都是天上的一颗新星。”
她闭上眼,默默许下一个念头:
>“愿所有未被命名的痛,都有人愿意倾听。
>愿所有被抹去的名字,都能在某个人的心跳中复活。
>愿我们不必成为神,也能学会如何爱人如己。”
不知过了多久,手机再次震动。是安娜从肯尼亚发来的视频消息。画面中,她站在新建的“记忆教室”前,身后是一排用回收木板搭建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孩子们手写的“祖辈故事集”。
“我们今天讲的是‘沉默的战士’。”安娜对着镜头微笑,“一个十三岁女孩讲述了她曾祖母的事??那位老妇人在殖民时期藏匿反抗者,却被家人指责‘惹祸’,死后连葬礼都没有。今天,全班同学一起为她补办了一场追思会,念了悼词,唱了她最爱的歌。”
她顿了顿,眼神明亮:
“谢峰成,你知道最动人的部分是什么吗?
那个女孩说:‘我现在终于敢告诉我妈妈,我也想成为一个让她骄傲的人。’”
视频结束,屏幕上留下一行自动添加的文字说明:
>“本日全球新增记忆行为:4,872次
>覆盖国家:93
>最高频词汇:‘我记得’‘对不起’‘谢谢你’”
谢峰成靠在长椅上,望着星空,忽然笑了。眼泪顺着脸颊滑落,但她不再擦拭。
她知道,这场战争没有终点。
权力仍会篡改记录,资本仍会消费苦难,人群仍会在热闹中遗忘。
但此刻,在这个寒冷的城市角落,在千万个相似的夜晚里,有人正翻开旧日记,有人正拨通十年未联系的电话,有人正对着坟墓说出憋了半辈子的话。
他们不是在召唤神明。
他们是在成为光本身。
她站起身,拍掉衣服上的雪屑,将希望号小心收回背包。路过一处公交站时,发现站牌背面被人用马克笔写下一句话:
>“如果你感到孤独,请相信??
>somewhere,someoneisrememberingsomeonejustlikeyou。”
她驻足片刻,从包里取出记号笔,在下面添上一句:
>“AndIamhere,rememberingwithyou。”
然后转身离去,脚步坚定,踏碎一路残雪。
夜风拂过树梢,吹动一片枯叶,轻轻覆盖在那两行字上,像一封未曾寄出的信,终于找到了它的封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