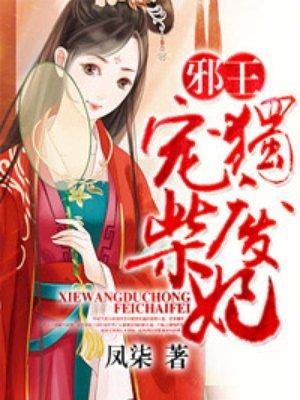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张大千传(高阳版) > 十 敦煌行(第2页)
十 敦煌行(第2页)
我的答复是肯定的。湖南人名为资生,自是生于资水,而非四川的资中、资阳。资水有南北两源,南源叫夫夷水,又称罗江,也就是汨罗江,流经湘阴东北,其地有村名汨罗村,即屈原自沉之处。《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则以湘阴人名资生字孝畹,完全合乎中国传统命名的原则。当然,高拜石知道有蒋孝畹其人,是必有来历的。
我的假设是,当年跟张大千谈敦煌石室发现经过的人,可能把上声“养”韵的蒋,误为平声“阳”韵的杨。如果我的假设不误,则斯坦因第一次私探千佛洞,不是蒋资生陪了去的。他既有调查地理的任务,自然要雇用翻译。倘谓此第一次的翻译即是蒋资生,那就根本不必找年轻喇嘛细问经过。如何发现石室,“全本西厢记”都在他肚子里,立即就可以策划盗宝了。
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原著,我未读过。据高拜石文中所引,斯坦因在初探与“再来”之间,如果未曾叙述如何访得蒋资生的经过,则杨先生就是蒋资生,更可肯定。盗宝的实情是,斯坦因找到蒋资生以后,并非如高拜石所说“伴他去找王道士,曲意结交”,而是先由蒋资生去跟王道士打交道,原则谈好了,斯坦因才又去的。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说:
“当我再来的时候,王道士已回来,并且在那里等候了。他当然知道他保管的是什么,但也充满了有关宗教方面的恐惧,说话是那么吞吞吐吐的。当我们见面时,我便觉得这个人有些不易捉摸,我只得尽我所有的金钱,对他以及他的寺庙进行诱引。终于这道士被我的话打动了,悄悄地答应等入夜时把密室所藏的中文卷子中拿出几卷来,交给我的助手,以供我们研究。”
说王道士已在“等候”,可知事先已有联络。至于王道士的吞吞吐吐,无非忸怩作态;而“拿出几卷来”“以供研究”,只是先提供样品,以便看货论价。斯坦因又记:
“透过我的热心助手的帮忙,很侥幸地说动了王道士,使他勇气为之大增。那天早晨,王道士带了我们,将通至藏宝的石室一扇门打开,在黑黝黝的石室中,道士手里所持昏暗的油灯微光,使我的眼睛忽然为之豁然开朗。”
这是当夜看过“样品”以后,第二天上午的行动。王道士的“勇气大增”,当然是银子壮胆之故。石室中的情形,据斯坦因形容,“在约有九尺见方的小室中,站了两人进去,已没有多少余地。只见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乱堆在地面,高达十尺左右”。在这狭窄的空间中,施展不开,所以王道士允许将经卷拿到新建佛堂的一间小屋子里,把布帘密密遮了起来细看。王道士经“开导”以后,很热心地一捆又一捆地捧了来。至此,斯坦因不但登堂入室,而且予取予求了。
斯坦因第一天所看到的宝藏,第一是用“很坚韧的纸张”所写的中文佛经,“全部保存得很好”,与初入藏时无甚差异。经卷尾端写有年代,计算“约在纪元后第五世纪的初年”。此为陶渊明归隐、南朝由宋而齐、东昏侯被弑的一百年,北朝则正是北魏倾心汉化,发展出陈寅恪所颂赞的“太和文化”时期。
第二是许多西藏文写本,时期约为“第八世纪至第九世纪中叶。石室之被封闭时期,可能也在这一时期之后不久”。这个算法,可能有误。九世纪中叶,应为唐朝开成、会昌、大中诸朝,虽有牛李党争,国势尚不甚衰。封闭石室是十一世纪之事。
第三,也是最令斯坦因“高兴”的“一些古画”,绢上画的“全是美丽的佛像,颜色调和,鲜艳如新”。
至此,斯坦因所考虑的,只是量的问题了。他说他最注意的,“是从这惨淡的幽囚以及现在保护人漠视的手中,所能‘救’出的,究竟能有多少?”
问题很单纯,王道士能给多少,他就能救出多少。而王道士有一种人言可畏的心理,而纠正他这种心理的特效药,依旧还只是银子。以下便是表扬“蒋师爷”的功劳了:
“到了夜半,‘忠实的’蒋师爷自己抱了一大捆的卷子,来到我们所住的帐篷内,那都是第一天所挑选出来的东西。我真高兴极了。蒋已经和王道士约定,在我未离中国以前,这些‘发现品’的来历,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任何人不能让他知道。”
为了保密起见,盗宝的工作在每天晚上进行,而且由蒋资生不辞辛劳,亲自搬运。连着七个晚上,方始告一段落,完整的经卷一无孑遗。据张大千所知,完整经卷恰好一万,完好无缺的画,亦达五百张之多,斯坦因是雇了四十头骆驼拉走。至于王道士所得,实际上只不过几百两银子。蒋资生当然也捞了一票,数目就不知道了。
这些经卷,斯坦因将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在印度,成立西域博物馆,而精品则入藏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深知其事,紧接而来。他的收获在量上不及斯坦因,而质却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他是内行,特别注意古书及文献。然而就量来说,亦颇可观了。
谢稚柳所著《敦煌艺术叙录》中说:“伯希和到北京,颇扬言于士大夫间,谓吾载十大车而止,过此亦不欲再伤廉矣。”外国人尚知廉耻,反而中国的士大夫不知廉耻为何物。谢稚柳又记载一段内幕:
“宣统元年,北京学部始令甘肃省将余经缴北京,则仅八千卷而已。初,学部要新疆巡抚何彦升(字秋辇)代表接受此项经卷,以大车装运北京。当车至北京打磨厂时,何彦升之子何震彝(字鬯威)先将大车接至其家,约同其岳父李盛铎(字木斋)、刘廷琛(字幼云)及方尔谦(字大方)等,就其家选经卷中之精好者,悉行窃取,而将卷之较长者,一拆为二,以充八千之数。事为学部侍郎宝熙所悉,谋上章参劾,会武昌起义,事遂寝。”
李、刘、方三人,皆为当时学术文化界名流。方尔谦是扬州人,为袁世凯幕友,与袁寒云以师弟而为儿女亲家。李盛铎是江西人,曾任驻日公使,为有名藏书家。刘廷琛则首任京师大学堂监督,为人师表者如此!
敦煌石室的宝藏,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具有无比重要的影响。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部分来谈,一部分是失传的作品,如唐朝末年盛行虽讲平仄韵脚,但文白如话,比老妪都解的白居易的诗更进一步的通俗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作家王梵志,他的诗就是在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其中有一首是:“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红楼梦》中妙玉所说:“纵有千年铁门坎,终须一个土馒头。”向来以“土馒头”为坟墓的代名词,却不知其出处,王梵志诗出,算是寻着“娘家”了。
另一部分便是“变文”。在此以前,留意中国文学源流的人,对于汉赋、六朝骈体、唐诗、宋词、元曲演变的轨迹,能说得清清楚楚。但是,纯以文言所写的唐人传奇,为何一下子转变为宋朝用白话演义的平话,却无能言其故。自从变文出现,才知道中间有此一道桥梁。
变文是用韵文与散文合组的一种文体,源自印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弘扬佛法的重要工具。所谓“变”者,“变相”的简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对壁画的“变”曾有详细解释,吴道子即以善绘“地狱变”知名。敦煌壁画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名为“经变图”,为“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降魔变”等等。每一“变”中,又分门别类,描写一个完整的故事。不道“变相”不但是绘画的题材,更是文学与音乐的题材,那就是变文。
何以说变文也是音乐呢?因为变文中属于韵文的部分,是可以唱,也需要唱的。《乐府杂录》记唐朝中叶一僧云:“长庆中,俗讲僧文叙,善吟经,其声宛畅,感动里人。”赵璘的《因话录》,记文叙的魅力,真是“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变文的发现,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一个是罗振玉,一个是刘半农。不过,罗振玉之功是否为王国维的成就,犹当存疑。罗振玉自伯希和处取得若干资料,又自学部所收敦煌宝藏残余中获得若干实物,著有《敦煌零拾》一书,所收“佛曲三种”即为变文。因论及宋人“说话四家”,其中“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谓参禅”,不知其所本者,观佛曲始知“此风肇于唐而盛于宋两京(指开封及杭州)”。
刘半农是法国留学生,他从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得不少伯希和弄走的敦煌卷子,刊为《敦煌摄琐》之辑,其中变文很多。因为有了这些丰富材料,从事文学史的学人才能作有系统的研究。
变文大别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敷演佛经故事;一类是与佛经无关,而大致皆以历史上的名人作题材。后者便摆脱了宗教的色彩,而成为文艺的一种新形式。如《伍子胥变文》,合伦敦、巴黎两处的收藏,已得全文的百分之七八十,情节相当完整。伍子胥的故事,除了《史记》《越绝书》中记载以外,“变文”中又增添了许多,加上了姊姊及两个外甥。还有一段,伍子胥叩门乞食时,遇见他的妻子,但因伍子胥是在逃亡之中,彼此都不敢相认。然则又何以通情愫呢?是以药名做隐语通问,文字半文半白,如言楚王“忽生虎狼之心”一段:
“楚王太子长大,未有妻房,王问百官:‘谁有女堪为妃后?朕闻国无东宫半国旷……太子为半国之尊,未有妻房,卿等如何?’大夫魏陵启言王曰:‘臣闻秦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丽过人,眉如尽月、颊似凝光、眼似流星、面如花色,发长七尺,鼻直颜方……’遂遣魏龙陵召募秦公之女。楚王唤其魏陵曰:‘劳卿远路,冒涉风霜。’其王见女姿容丽质,忽生虎狼之心。魏陵曲取王情:‘愿陛下自纳为妃后,东宫太子,别无外求。美女无穷,岂妨大道?’王闻魏陵之语,喜不自升(胜),即纳秦女为妃,在内不朝三日。伍奢闻之愤怒,不惧雷霆之威,披发直至殿前,触圣情而直谏。”
这段驳杂不纯的文字,介乎唐人传奇与宋人话本之间,桥梁的功用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变文”题材以佛经故事为主,最常用的一种形式是,首引经文三两句,以下就是演义,想象力的丰富,实在惊人。如最有名的一部《维摩诘经变文》,虽然完整的只有三卷,但其中一卷标明为“第二十”,还只讲到“问疾”,原文的长度如何,简直有无从估计之感了。
维摩经的全名为《维摩诘所说经》,传世有三种译本,而以鸠摩罗什所译的一本最流行。维摩诘是人名,为佛在世时的一个大居士。维摩诘是梵文,义译为“净名”,净者清净无垢,名者声名远著。如果嫌净名深奥了一点,可以改译为“清誉”。王维字摩诘,即是以维摩居士自居。张大千当然读过这部一向列为文学名著的《维摩经》,而且不但向往维摩居士,作为亦与维摩相近。因此读他的敦煌之行,应该谈一谈维摩的趣事,两者是有因缘的。
维摩的趣事,只见于变文中。变文首引经文一两句,字数不足二十,但能敷演出三四千言之多,因此,《维摩诘经》的一卷在《维摩诘经变文》中,便化成十几二十卷。如《维摩诘经》中“文殊师利问疾第五”,本为一卷,但变文中“文殊问疾”变成了独立的篇名,罗振玉藏有第一卷。而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维摩诘经变文》第二十卷,实际上为“文殊问疾”的第二十卷,且还只在如来佛遣门弟子的阶段——维摩口角犀利,好捉弄人,个个害怕,最后才在勉为其难的激励下,由以智慧著称的文殊应命。
像如来佛遣其弟子——亦为从弟——多闻称第一的阿难问疾。阿难推辞云:
“世尊,我不堪任诣彼问疾。所以者何?忆念昔时,世尊身有小疾,当用牛乳。我即持钵诣大婆罗门家门下立。时维摩诘来,谓我言:‘唯,阿难,何为晨朝持钵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有小疾,当用牛乳,故来至此。’”
阿难说的是实话,维摩却偏说他撒谎,意中指阿难借名来募化不易得的牛乳。他那套理由能说得阿难怀疑自己是不是将佛的话听错了——“得无近佛而谬听耶?”维摩诘的话是:
“止,止,阿难,莫作是言。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会,当有何疾?当有何恼?默住,阿难,勿谤如来。莫使人闻此粗言,无命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语。阿难,转轮圣王以少福故,尚得无病,岂况如来无是佛会,普胜者哉?
“行矣!阿难,勿使我等受斯辱也。外道梵志,若闻斯语,当作是念:何名为师?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诸疾人?可密速去,勿使人闻!当知,阿难,诸如来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为世尊,过于三界。佛身无漏,诸漏已尽;佛身无为,不坠诸数。如此之身,当有何疾?”
结果是如来佛亦觉得“维摩诘智慧辩才若此”,阿难不是他对手,问疾会不得要领。于是,改派他人。而他人亦有一套“不任”的原因,个个不同。变文设想巧妙,仿真维摩的语言神态,极其生动。可惜,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作者却失传了。但也很可能是集体创作,即由演唱的和尚一次一次逐渐修改而成。
当然,张大千对敦煌最感兴趣的是画,色彩鲜艳如新的绢画,大部分为斯坦因捆载西去;小部分散落民间,难得一睹。但就龙沙四窟——敦煌城南的莫高窟、城西的西千佛洞、安西城南的榆林窟及水峡口,约计三百余洞的壁画犹在,是外国人所盗不走的。不过,那时候的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了解并不多。
敦煌之以壁画驰名中外,已成常识。但说实话,在我未接触到这些史实以前,不知道敦煌为何有那么多的壁画,竟致有“千佛洞”之名,以及这么多的壁画,井井有序地排列着,是否有官员负责安排与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