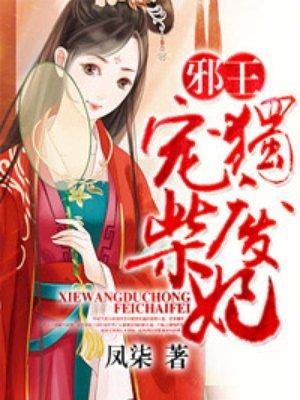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张大千传(高阳版) > 十 敦煌行(第3页)
十 敦煌行(第3页)
先解答后一个问题。据敦煌学家陈祚龙的考证,确有一个专门处理壁画制作事务的官方机构,其名为“画行”。然则“知画行”应是管理画行的首脑。“知”即主持之意,唐宋官衔中常用此字,流传到后世,就只剩下知府、知县,以及主持会试的“知贡举”了。
陈祚龙在《莫高窟壁画表隐》一文中又说:“就在这种‘画行’之中,尚有专门负责供应有关制作‘材料’的官员。这样的官员之‘雅号’,虽为‘都料’,但他们什九皆为当年大家公认是学有传承的绘事‘老手’。”这一点,恐怕稍有问题。“料”是材料,“都”为聚集之意,“都料”即是管理材料的主官。陈祚龙所引例证:归义军节度押衙董保德等修《功德记》文中,有“厥有节度押衙,知画行都料董保德等”一语,情况是很明白的,他的本职是“节度押衙”,掌管警卫仪仗,必然是归义军节度使的亲信。押衙一职,常由武将担任,似乎不应是个“绘事老手”。
《功德记》是一篇骈体文,其中有一段说:“家资丰足,人食有余。乃与上下商议,行旅评剖。君王之恩隆须报,信心之敬重要酬。其修功德,众意如何?寻即大之与小、尊之与卑,异口齐欢,同音共办。”这就是造壁画的缘故,意在报恩敬佛。
但紧接在下面的一段话,大可玩味:“保德自己先依当府子城内、北街西横巷东口敝居,创建兰若一所。”兰若为梵文阿兰若的简称,意为僧人聚居之处,就“敝居创建兰若”,即是“舍宅为寺”。此风自北朝至唐,一直盛行,《洛阳伽蓝记》中的静刹,大半为达官贵人的园林。
以下描写他所“创建”的“兰若”:四廊“图塑诸妙佛铺”,屋顶四角有瓴,后面还有一座佛塔。确是一座寺院建筑物的规模。但人人造一座“兰若”,势有不可,因而简化为找一个洞窟,画上壁画,或者画一幅佛像,悬在洞壁上,即已表达了报恩祈福的心愿。
这种绢画,张大千收藏有两幅,皆为隋画,现已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大风堂遗赠名迹特展图录》中,编为第一号、第二号。次序是颠倒了,因为第二号成陀罗造《观世音菩萨像》,款署“仁寿三年癸亥十一月,清信弟子成陀罗为亡女阿媭造”,仁寿是隋文帝的年号。第二幅《释迦牟尼像》,造于隋炀帝大业五年己巳,晚了六年。
另一可能是在敦煌所购。苏莹辉于抗战期间,服务于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曾听人谈起,研究敦煌学很出名的向达第一次到敦煌时,由当地县政府一个任科长介绍,搜购石室唐人写经及旛画。由于物主索价太昂,未能成交,仅买去不太值钱的五代写经残卷一两种。
到了民国三十三年夏天,向达又到了敦煌,想买上次看中的一幅绢画及两卷相当完整的唐人写经时,所得到的答复是:“已被张夫子出高价买去了。”张夫子是本地人对张大千的尊称。苏莹辉说:“向张之不睦,肇因于此。”据说:“当时在敦城士绅,或经商人家,涉及买卖石室宝物事宜的,双方皆讳莫如深。”因此,苏莹辉并未跟向张二人谈过此事。
再有一个可能是战前在北平所得。“受馈赠或价购,或以书画互换,皆有可能。”但照情理来说,自以购自敦煌的可能性最大。张大千的敦煌之行,由于无意间开罪于人,以致蒙谤,这或者就是张大千所得的这两幅隋画虽然来路清白,但为免得惹起他人无谓的猜疑起见,从不谈此事的缘故。
对这两幅隋画,张大千视如瑰宝,当然不是因为它值钱。事实上他既不谈此画,则是很明显地早就决定将来以此画捐献予台湾。书画割爱,如何可得善价,张大千是太内行了。倘或他有意待价而沽,当然先要放出风声去,歆动豪富的收藏家。不此之图,就是根本无此企图。
那么它珍贵在什么地方呢?珍贵在这两幅画是世界上最古的画。隋文帝仁寿三年,正当七世纪刚开始的公元六〇三年,让我们放眼世界看一看:欧洲,希罗文化在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尽遭破坏而宣告死亡,正处于“黑暗时代”;中东,伊斯兰教尚在秘密宣传阶段,要到公元六一二年,也就是隋炀帝大业八年,初征高丽失败的那一年,穆罕默德方始公开传教;日本是在“大化革新”之前的“飞鸟时代”,当时连“日本”这一国名都还没有,中国称之为“倭”,日本自称为“日出国”——唐高宗咸亨元年,即公元六七〇年——倭始改国号为日本;印度,笈多王朝业已崩溃,归附于戒日王朝——笈多王朝为印度史上黄金时代,文学、艺术、科学,至为发达,但阿禅多佛洞精细绝伦的壁画,对敦煌壁画固有直接的影响,却未闻有绢画传下来。
已故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庄严在他收入《山堂清话》的一篇《我与三希帖的一段缘》中说,《中秋》《伯远》两帖,传说为清德宗[1]瑾妃私下送至北平后门外小古董铺“品古斋”售去,辗转流入郭世五之手;《快雪时晴帖》则以名气太大,故得幸存,现仍珍藏于外双溪。民国二十二年,由于北方局势日紧,倘有战祸,国宝被毁,因而指令“故宫博物院”将文物南迁。
第一批由庄严负责押运。临行前,郭世五为庄严饯行,同时也请了庄严的顶头上司、“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此人字森玉,其子即张大千的“经纪人”之一,以鉴赏知名的徐伯郊。
台北“故宫博物院”于民国五十四年双十节成立时,下设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四库全书及历代藏书由图书馆典藏;档案、图像以及实录起居注等等,由文献馆执掌;此外一切书画古董,都归古物馆管理。庄严其时为此馆科长,见多识广,与北平收藏家无不相熟,生前曾跟笔者谈过郭世五与刘禺生在《洪宪纪事诗簿注》中的记载有异。
郭世五是河北定兴人,据说他是袁世凯的“外账房”,专管袁世凯的私人支出,也就是不足以为外人道的秘密开销。他的官职则是九江关监督。此人对瓷器研究颇具心得,因此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被聘为专门鉴别瓷器部门的委员。庄严在他所著的《山堂清话》中说:
“民国初年,袁世凯意图称帝,为纪念登基而预烧的那一批落‘居仁堂’款的洪宪瓷,就是由郭世五在江西景德镇筹划监制的。所谓居仁堂是当时坐落在北平中南海总统府内袁氏家居的斋堂名称,而办公的地方则称怀仁堂。因为袁在民国四年烧制这些瓷器的时候,尚未拟定次年欲登基的年号,再说,即使已决定登基的年号为‘洪宪’,当时也未必敢明目张胆地落‘洪宪年制’的款。因此,凡落有‘洪宪年制’款的洪宪瓷,实为后人仿制、欺瞒世人的赝品。”
洪宪瓷而有赝品,其珍贵可知,而所以珍贵,别有缘故。据说郭世五常打着袁世凯的招牌,至“旁观者清”的“大内”,索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烧制,专供“上用”的瓷器,刻意仿制,乃成精品。亦就因为他有此可以打袁世凯的招牌的便利,与“小朝廷”的太监及“内务府”相熟,清宫中许多被盗卖的宝物落入他手中,是很自然的事。
“三希”中的《中秋》《伯远》二帖之能归于郭世五,当然亦是有太监通消息,才能捷足先得。据庄严说,那天饭罢欣赏他的珍藏时,郭世五曾当来客及其子郭昭俊的面说,在他“百年之后,将把他拥有的此二希帖,无条件归还故宫(博物院),让《快雪》《中秋》《伯远》三希帖再聚一堂,且戏称要我届时前往接收。”
结果是,郭昭俊携此二帖离台赴港,不知何人居间,售予外人。《伯远帖》在香港有影印本出售。
可是,据庄严的研究,“三希帖”亦并非真正的稀世奇珍。他说:“《快雪》《中秋》《伯远》三希,以《快雪帖》最负盛名,现在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曾多次陈列出来,供国人观赏。它是唐摹本,并且从它的行笔来看,不是出于书写,而是出自双钩廓填,以其在书法本身价值来评,我认为其钩描的线条涩而不活,填墨浓重而缺神气,乾隆御题‘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实在夸奖过了一些。其次是《中秋帖》,我也疑惑它出自宋米南宫[2]之笔。纵观历朝各代书法的时代风格,及各个书家的体貌个性,总觉得《中秋帖》那种连绵草书,与晋人书写的字字独立、笔笔中规的章草(隶书的简笔字)风貌不合。像帖中那种墨迹的运笔方式,到唐初尚不多见,至张旭以后才开风气,宋米芾喜爱如此运笔,而且甚具气象。”
《快雪帖》为唐人双钩廓填,《中秋帖》疑出米芾之笔,至于《伯远帖》,照庄严的形容:“运笔之潇洒淋漓,线条之粗细变化自在,以及整体之动态韵律起伏,都是被一般书家所称道的。”则显然亦是“草圣”张旭以后的风格。
由此可见,说张大千的那两幅隋画为存世最古的墨迹,并不过分。倘谓马王堆的帛书更古于此,这话并不能成立。隋唐的绢书,能保存至一千两百余年之久,是因为敦煌石室在地理、天时上的特殊优越条件。纺织物入土两千年不腐,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无可疑地,敦煌石室的绢书,在张大千未到敦煌以前就曾见过。也许这是激发他作敦煌之游的动机之一,但非全部。
张大千之决定远游敦煌,动机相当复杂,换句话说,是多种因素汇合而促成的。原始的动机,也许只是静极思动,但此时他多少仍还存着遁世的观念,入山既唯恐不深,则出游必不辞路远。至于想到敦煌,是记起了叶恭绰劝他专攻人物的话。不过做此远游,并不表示他接受了叶恭绰的劝告,只是想看一看那些壁画到底有多少值得学的东西。此外,不能也不必讳言地,或多或少地有着一种炫人耳目的作用在内。
在我个人的看法,张大千在敦煌作艺术上的“苦行僧”,精神上与玄奘西域取经有相通之处,表现了他的勇气、毅力及对艺术的虔敬。他在敦煌两年有余的生活之本身,便是一大成就。
两年七个月是就前后两次合并计算。张大千谈他初临千佛洞的情形说:“千佛洞离敦煌的四十里路很奇,有十里绿洲、十里戈壁,再行二十里沙碛方至。是地气候,白昼酷热,不能行路,行旅要在半夜动身,清晨赶到。千佛洞四周树木蓊郁,流水环绕,但里外即石碛遍地,黄沙逆风,不见茎草。”这天清晨,张大千拂晓到达千佛洞,迫不及待地提灯入洞,“这一看,”他多少年后追忆,仍是惊叹的口吻,“不得了!比我想象中不知伟大了多少倍。原定计划是来此三月观摩,第一天粗略看了一些洞,”他对从行家人说,“恐怕留下来半年都还不够。”
结果是待了七个月,杨宛君要回成都了。张大千劝她仍旧留下来,他说:“你不是说嫁了我之后,就是我‘讨口’,你都要跟我一路吗?”四川话“讨口”是讨饭的意思。
杨宛君坚决不愿,她的理由很妙。她说:“我只有一个理由,我跟你来敦煌七个月,除了我自己是女人以外,我还没有见过第二个女人。”于是第二次去,有了“第二个女人”,那就是最先进张家门的黄凝素。
这七个月中,张大千主要的工作是为五层三百余洞窟编号,及策划重来做长期逗留的工作。其中必须一记的大事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视察西北时,特为迂道至敦煌,与张大千共度中秋。那年于右任六十三岁,未见衰老,到了敦煌,流连忘返,张大千还为他在烧残的垃圾堆中,发现索靖的“日仪”墨迹残字。两髯日日结伴看壁画,有一天看出事来了。
据于右任的随员且是敦煌土著的窦景椿,在纪念张大千的一篇文章中说:“民国三十年夏间,我随于右老由兰州前往敦煌,尔时大千先生居留千佛洞,陪同右老参观如洞壁画,随行者有地方人士、县府接待服勤人员,及驻军师长马呈祥等人。记得参观到一个洞内,墙上有两面壁画,与墙壁底层的泥土分离、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地,并有挖损破坏的痕迹。”
窦景椿又说:“因过去信佛者修建洞壁画像,尝把旧洞加以补修,改为己有,但此洞原有画像,欲盖弥彰,从上面坏壁的缝隙中,隐约可见画像的衣履,似为唐代供养佛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释,右老点头称赞说:‘噢,这很名贵。’但并未表示一定要拉开坏壁一睹。当时县府随行人员,为使大家尽可能看到底层画像的究竟,手拉着上层张开欲裂的坏壁,不慎用力过猛,撕碎脱落,实则亦年久腐蚀之故。”
这是窦景椿所目击,连于右任说了一句什么话都记了下来,真所谓指证历历,堪为信史。原来从北朝以来,壁画日积月累,凡能画的地方都画到了,后人欲做功德,便出一下策,即在原来的壁画上,用中国传统补画的办法,用麻筋搅和黏性泥土,涂抹一层,再用石灰浆刷白,绘画其上。此壁是当时施工不良,黏附不固,年深月久,加上人为的破坏,剥落游离,以致“撕碎脱落”。
这虽是无心之失,却是歪打正着。有许多记载,说这浮面的一层,是张大千跟于右任商量以后,命马呈祥的士兵打掉的。衡情度理,正确的事实应该是,既然已“撕碎脱落”,那就索性彻底清理干净。这个洞在张大千编号是“第十二窟”,高八丈五尺、深二丈四尺、广五丈三尺,经彻底清理后,南北两壁出现的,果然是唐画。据谢稚柳《敦煌石室记》著录:“北壁男像四身,后有持杖佛等四人;南壁女像三身,后女侍九人。北壁男像第一身,乌帽青袍束带,须髯甚美,擎一长柄香炉,高六七寸。”此人即是做功德的“供养人”,为当时的“晋昌郡太守乐庭瑰”,南壁女像第一身为他的妻子“太原王氏”。
所谓“北壁”“南壁”是怎么回事?不明千佛洞——莫高窟的形象背景,不易明了。手头恰好有个美籍华裔的吴小姐在去年游敦煌所写的游记,是最新的数据,可以介绍。她说:“整个莫高窟由南到北,长达二千六百米,看起来像蜂窝一样的洞窟,密密层层、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地排列在陡峭的灰色崖壁上。洞窟前有一道细长的流泉,水边长着茂盛的树林及一些耕地。”又说,“每一个洞窟都很阴凉,除非正是阳光照入的时候,平常看进去,都是漆黑一片。”
由乐庭瑰的官衔,可知为唐朝人。敦煌之西的安西州,唐朝名为晋昌郡,大历十一年陷于吐蕃,七十年后始收复。据谢稚柳的考证:“这幅壁画是唐开元、天宝年间所作,对考据唐代艺术,帮助很大。”又说,“天宝之唯一可证者,为第二十窟。”至于壁画外层的清除,谢稚柳表示:“要是你当时也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得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打掉了,来揭发内层的精华呢?”于此可以肯定,第二十窟外层打掉,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有益无害的。
但当时对张大千来说,却带来不小的伤害。据窦景椿记,当时“适有外来的游客,欲求大千之画未得,遂向兰州某报通讯,指称大千先生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古物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辨”。窦景椿说,他来台后还“闻人谈及”。笔者亦几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说张大千在敦煌盗宝,有这话没有?”因此,对这重公案的经过,我必须根据客观的资料,做一详细的叙述。
当时中伤张大千的流言很多,据张大千多少年后对人表示:“一言难尽。”不过居然有人说杨宛君还“夹带了一只死人的手骨回来”。虽事隔多年,张大千提起来犹有余恨。
[1] 即清朝的光绪皇帝。
[2] 即北宋书画家米芾。他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做过礼部员外郎、书画学博士。唐宋时对在礼部管文翰的官又称作“南宫舍人”,所以后世也称他“米南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