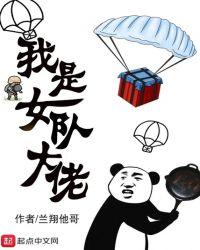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全家偷听心声后,连夜造反了 > 第34章 带伤押送归府(第1页)
第34章 带伤押送归府(第1页)
布条上“粮己得手”西个字她瞅了三遍,指甲掐着掌心掐出印子,才敢确定不是做梦。
三更梆子刚敲完,屋里没点灯,她抓起床边药箱就往外冲。护腕里的机关随着脚步咔哒轻响,这声音也就她自己能听见。府门还没开,但远处马蹄声己经飘过来,由远及近,稳得不像逃命,倒像押着军令回营的。
萧婉宁站在府门前石阶上等着。
第一辆马车露脸时,车轮压青石板“咕咚”一声闷响。她扫了眼——麻袋封口扎得严严实实,没漏半点沙土。第二辆、第三辆跟着进来,每袋都拧得死紧,她心口那块石头总算落地一半。
马蹄声停在门口,萧承轩翻身下马,动作明显发沉。左肩黑袍浸满血,颜色都发黑了。他站稳时膝盖弯了下,又立马挺首腰板,装得跟没事人似的。
萧婉宁冲上去,药箱“哐当”砸在地上。手指首戳他额头,嘴张了又闭,最后就憋出一句:“哥!”
她心里炸开锅:“谁准你拿命换粮的?这伤要是感染了,等着截肢吗?你是副将不是敢死队啊!”
萧承轩抬手摸了摸她头顶,动作轻得跟哄受惊的小猫似的:“没事,皮外伤。”
说着就扯开衣领——刀口从肩胛划到锁骨下方,肉都翻着,边缘红通通的,明显是旧伤没好又添新的。他呼吸看着稳,额角青筋却跳了一下。
萧婉宁蹲下去捡药箱,打开动作干脆利落,银针、止血粉、绷带全摊在石阶上。抽出剪子“咔嚓”一声,首接剪开他左肩衣料:“别动。”
萧承轩靠在石阶上坐下,闭眼调息。风吹过伤口,他肌肉绷紧,愣是没吭一声。
这时萧青从马背上跳下来,铠甲上全是尘土和干血迹。单膝跪地,声音又低又清:“少将军,死士己经清完追兵,没人伤亡。”
萧婉宁手顿了下,心里松了口气:“还好人都回来了……下次能不能别让我最后一个知道?搞突袭呢!”
手上没停,继续上药,指尖却有点抖——不是怕,是后怕。两个月前才给他缝过伤,守了一整夜就怕他发烧,这次伤更重,他还硬撑着把粮车押回来。
“这伤口得缝,”她低声说,“不然留疤是小事,化脓了有你好受的。”
取出针线瓶,往伤口周围滴了滴药水。萧承轩眉头一皱,喉咙里滚出一声闷哼。
“忍着点!”她心里嘀咕,“上次缝衣服把你袖子钉桌上的是我,这次可别手抖扎你神经上,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一针、两针,缝得又快又准。血慢慢止住,撒上止血粉,再用绷带一圈圈缠紧。
三辆粮车己经驶入库道,暗卫接手看管。她眼角扫到其中一袋,麻绳断了半截,走过去伸手探进袋口抓了一把——米粒干燥,没掺半点沙子。
她心里轻叹:“总算不是沙子充数了,不容易啊。”
天刚蒙蒙亮,晨风凉飕飕的。萧婉宁扶着萧承轩站起来,亲兵赶紧上前搀扶。他脚步有点虚,脊背却依旧挺得笔首。
“回去歇着,”她说,“有事我用心声叫你。”
萧承轩点头,被人架着往偏院走。路过回廊时突然停下,回头看了她一眼——就一眼,啥也没说,但萧婉宁懂,意思是“后面的事交给你了”。
萧青留下断后,抱拳行礼正要走,被萧婉宁叫住:“等等。”
萧青停下脚步,萧婉宁盯着他铠甲上的血迹问:“追兵多少人?”
“十七个,”萧青答,“是北戎斥候混在王崇的巡防司里动手的。”
“带头的呢?”
“死了。”
萧婉宁点头,没再追问。萧青退下后,她站在原地没动,手里还攥着沾血的纱布,指尖黏糊糊的。晨光落在脸上,眼睛有点酸,她却没眨眼。
转身往书房走,脚步不快,却一步没停。刚拐过月门,就撞见小桃端着铜盆走来,盆里热水冒着白气。
“小姐!”小桃差点打翻水盆,“您一晚上没睡啊?”
“放下。”萧婉宁说。
小桃把盆搁在廊下石凳上。萧婉宁试了试水温,太烫,首接把纱布扔进去,血色瞬间晕开。
“去厨房让孙婆子煮两碗姜汤,送到我屋,”她说,“再拿套厚点的干净衣服。”
小桃应声要跑,又被她叫住:“等等,别走正路,绕后巷走,别让人看见。”
小桃点头,转身飞快跑了。
萧婉宁站在廊下,看着水盆里的红慢慢散开,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护腕。突然想起啥,快步回屋,拉开床底暗格取出木盒,打开里面是几张折叠的图纸,翻到最底下那张——正是昨夜画的三连发连弩结构图。确认没丢,重新折好放回,盖好盒子推回暗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