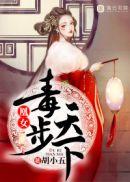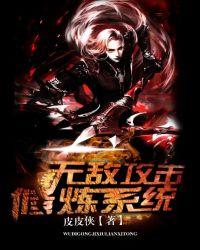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天唐锦绣 > 第二二三九章 机密资料(第1页)
第二二三九章 机密资料(第1页)
水陆两路大军相继攻陷泰西封城、摩苏尔城如同插入大食腹心的两柄尖刀,势必造成大食内部之动荡、恐慌,只需再做出厉兵秣马、锐意进取之姿态便足以逼迫大食前来和谈。
除非大食人都是一根筋,宁肯放弃与拜占庭。。。
沈言离开长安那日,天未亮透。城门尚闭,他却已立于渭水桥头,背影单薄如纸。晨雾弥漫,桥下流水无声,仿佛天地间只剩他一人独行。风从终南山方向吹来,带着泥土与枯叶的气息,拂过他的衣角,又卷起脚边一片泛黄的竹简残页。他弯腰拾起,只见上面歪斜写着半句诗:“声断处,魂归来。”字迹稚嫩,却不像是孩童所书,倒似一个久困喉中的人终于挤出的叹息。
他凝视片刻,将竹简收入怀中,转身踏上小舟。船夫是个老哑巴,满脸沟壑,只朝他点了点头,便撑篙离岸。沈言坐在船尾,望着渐远的城墙轮廓在晨光中褪成灰白,忽然觉得那巍峨宫阙也不过是一具巨大的声器??吞吐诏令,封锁民声,终将腐朽于时间之口。
舟行三日,抵达汉中。此处山势陡峻,溪流纵横,民间素有“九岭十八弯,一语传三村”之说。沈言本欲绕道南下岭南,却在途经一座荒废驿站时,听见林间传来断续铃响。那声音极轻,若非他耳力异于常人,几乎难以察觉。更奇的是,铃音节奏竟与阿禾生前常用的小调暗合七分。
他循声而入,拨开荆棘密林,见一破庙残垣伫立谷底,门前石阶裂作两半,香炉倾覆,蛛网横织。庙内佛像早毁,唯余半截莲座上搁着一只青陶铃,正随风轻摇。沈言走近取下,指尖触铃瞬间,一股寒意直透骨髓,耳边骤然响起低语:
“你还记得我吗?”
不是阿禾的声音。
这声音苍老、沙哑,像是多年未曾开口之人勉强挤出的气音,却又带着某种熟悉的韵律??如同《声迹图谱》中记载的“回溯共鸣”,唯有曾深度接触声器者才能触发。
沈言心头一震,反问:“你是谁?”
陶铃再度轻颤,那声音再次浮现:“我是第一个被缄口司剜去舌头的人……也是最后一个活着走出噬音鼎的人。”
沈言瞳孔骤缩。“不可能!鼎中之人只能以声核存续意识,肉身早已化为虚无。”
“你以为只有阿禾懂得献声?”那声音冷笑,“她不过是继承者。我们这些人,早在武周之前,就被选中成为‘容器’。他们称我们为‘缄者’,说我们是净化皇庭的祭品。可我们只是说了真话。”
沈言呼吸微滞。他忽然想起《声牢手记》末尾一页被撕去的痕迹,当时以为是岁月磨损,如今想来,或许另有隐情。
“你为何现在才出现?”他低声问。
“因为回音鉴响了。”那声音缓缓道,“七声钟鸣,唤醒了所有沉睡的声核。不止阿禾,还有我,还有三百零六名自愿或被迫献声者。我们的记忆并未消失,只是被封存在各地声器之中,等待一个能听见它们的人。”
沈言猛然抬头,环顾破庙四壁。忽见东墙裂缝中嵌着一块残碑,拂去尘土,依稀可见刻痕:“永宁三年,左拾遗崔明远,因谏获罪,削籍没声。”
永宁三年,距今已逾八十年。
“你们……一直都在?”他喃喃。
“我们在每一个不敢说话的夜晚,在每一场被焚毁的奏章灰烬里,在母亲哄孩子入睡时突然停住的歌谣中。”那声音渐转悲怆,“我们是沉默的代价,也是回声的种子。”
沈言双膝缓缓跪地,手中陶铃紧贴心口。他知道,自己错了一次又一次。他曾以为揭开噬音鼎的秘密便是终结,却不知那只是开端。真正的战争不在山洞深处,而在人心之间;真正的敌人不是某个权臣或制度,而是长久以来对声音的恐惧??怕它太响,怕它太真,怕它动摇根基。
他必须回去。
不为复仇,不为名声,只为完成阿禾未竟之事:让每一颗沉寂的灵魂都有机会说出最后一句话。
七日后,沈言重返长安。
此时京城风气已变。启声诏颁布数月,直言御史台每日收状如雪片纷飞,百姓争诉冤屈,士子热议政事。街头巷尾,私塾书院皆诵《百口陈情》,连小儿嬉戏也模仿廷辩之姿。然而,沈言一眼便看出繁华背后的裂痕??许多人说得太多,却无人真正倾听;言语自由了,心灵却更加喧嚣。
他在听心坊旧址重建“逆缄阵”,以带回的铜盘为核心,融合二十四处流动站传来的声波数据,试图绘制一幅《万灵声图》。林砚闻讯赶来,见他日夜不休地调试仪器,忍不住劝道:“你已做了你能做的。阿禾的愿望实现了,天下开始听见声音,何必再追那些早已消散的幽魂?”
沈言摇头:“正因为他们消散太久,才更需被召回。若任其湮灭,今日的自由不过是一场新的遗忘。”
穗儿也来了。她带来一箱旧物??那是她在洗心堂遗址翻找数日所得:几册残破日记、一方绣帕、一枚锈迹斑斑的官印。最底下,压着一封未寄出的家书,信封上写着“父启”,落款是一名戍边卒子的名字。打开一看,内容不过寥寥数字:“儿平安,勿念。昨夜梦见娘煮粥,香。”
穗儿眼眶红了:“这个人,可能早就死了。可他的梦还在。”
沈言将信纸轻轻放入共振仪中。当夜,玉牒投影出一幕影像:雪夜里,一名年轻士兵蜷缩在烽火台角落,手中握着半块干粮,低声哼着童谣。歌声微弱,却被风裹挟着,穿过千山万水,最终落入某个老妇人的梦境。
那一刻,整个听心坊的人都哭了。
自此,沈言定下新规:每月朔望,开启一次“招魂共鸣”,邀请各地百姓送来亲人遗物??一片布角、一支笔、甚至一口呼出的气,皆可作为媒介,尝试唤回其最后的声音。起初有人讥笑此举迷信荒唐,直到某日,一位老农送来亡妻生前缝衣针,竟在阵中还原出一段话语:“今年桃树开了七枝,你说要来看的……怎么还不回来?”
消息传开,万人空巷。人们终于明白,所谓“倾听”,不只是听活人的诉求,更是对死者尊严的守护。
然而,风波亦随之而起。
朝中有大臣上奏,称“招魂之举惑乱民心,恐引妖言横行”,请求禁绝此类活动。更有甚者,暗中派人潜入听心坊,欲毁去核心仪器。那一夜,穗儿值守,发现两名黑衣人正欲切断铜线,她奋起阻拦,却被击伤倒地。危急关头,林砚启动紧急共鸣,将附近所有陶片同时激鸣,声浪如潮,震得刺客耳鼻出血,仓皇逃窜。
事后清点,发现其中一人腰间佩牌刻有“内侍省监”字样。
沈言沉默良久,终是提笔修书一封,直呈皇帝。
信中不诉委屈,不论功过,只列三事:其一,回音鉴第七次鸣响时,播放的是一段宫中老宦官临终遗言,内容仅为“陛下幼时爱吃桂花糕”;其二,启声阁档案显示,近三个月共有四百一十三人通过招魂仪式找回亲人遗言,其中六十七人为平反冤案提供关键证据;其三,全国二十四站监测到,自招魂仪式推行以来,民间抑郁轻生之案下降四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