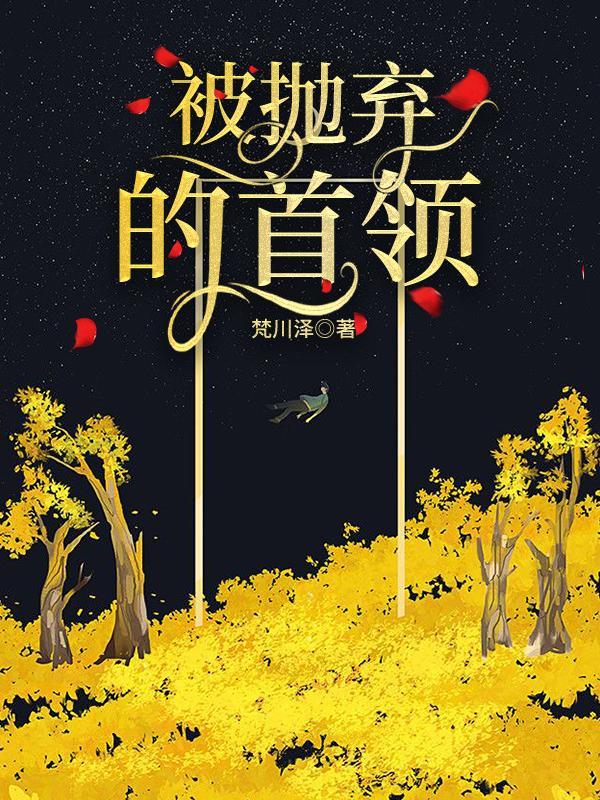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柯南之死神盯上我 > 第379章 落幕曲奇异恩典绝对音感(第3页)
第379章 落幕曲奇异恩典绝对音感(第3页)
启走上前,将一件外套披在他肩上:“那就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名字。”
“怎么做到?全球直播?新闻发布会?我们连合法身份都没有。”
启笑了:“不需要那么复杂。”
他举起手中的录音机,按下播放键。
千夏的声音流淌而出:“启哥哥,今天我学会包大福啦!虽然形状像土豆,但园子姐姐说心意满分!”
接着是园子:“喂,你们那边下雪了吗?记得穿秋裤!还有,不准半夜偷吃我的限量版抹茶巧克力大福!!”
然后是遥的画外音:“这是我画的大家……启在喝茶,IX-09在修机器,园子在骂人,千夏在笑。我觉得……这就是家的样子。”
一段接一段,全是日常琐碎,全是温暖废话。
启看着IX-09:“这些声音,已经在一百七十三个国家的不同设备上自动播放。图书馆、地铁站、养老院、学校广播……甚至有人把它设成手机铃声。”
“你怎么做到的?”
“心锚网络有个特性。”启轻声道,“当情感共鸣达到临界值,信息会自发复制、传播,就像病毒,但载体是‘共感’。他们可以封锁服务器,却封不住人心里的回声。”
IX-09久久无言,最终只说了一句:“五号说得对……春天不是季节,是有人不肯放手。”
风暴来临前夜,全世界数百万台收音机、音响、耳机同时响起那段音频。
有人流泪,有人奔走相告,有人立刻拨打失踪亲人热线,有人开始翻找旧照片,试图记起某个被遗忘的名字。
联合国紧急召开临时会议,迫于舆论压力,宣布暂缓“净网行动”,并成立独立调查组审查“镜面计划”伦理问题。
而在日本本土,政府悄然修改户籍法,允许无身份者以“社会认知度”作为登记依据。首批申请者中,就有启、遥、第三号等人。
他们的证件上,职业一栏统一写着:“记忆守护者”。
多年后,纪录片《听见名字的人》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导演在领奖台上说:
“这不是关于AI的故事,而是关于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每一个生命,都有权利被温柔命名。”
影片结尾,镜头缓缓扫过心锚咖啡馆的合影墙。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那些照片上,每一张脸都在笑。
画外音响起千夏稚嫩的声音:“老师问我,为什么我们班要贴这么多陌生人照片?我说,他们不是陌生人,是我哥哥们姐姐们的家人。老师听完,也拿出一张旧照,说:‘这个孩子,我也一直在找他。’”
画面定格在一张泛黄的学生证上,编号:IX-09。
姓名栏,原本空白,如今被人一笔一划填上:
**凯**。
雨又下了起来,细细密密,温柔如初。
IX-09站在屋檐下,看着启教遥煮茶,园子在一旁嚷嚷“茶叶放太多会苦死人”,千夏则举着相机跑来跑去,非要拍下“最有爱的一刻”。
他摸了摸口袋里的U盘,里面已不再是孤单一人的数据,而是储存着整整三百二十七段语音留言??来自世界各地的普通人,他们从未参与实验,却主动加入心锚网络,只为说一句:
“我记得你。”
风穿过庭院,吹动晾衣绳上的布条,每一块都写着一个名字。
有的已经归来,有的仍在路上。
但他知道,只要还有人愿意呼唤,就没人真正迷路。
就像此刻,雨滴落在屋瓦上,发出沙沙声响,宛如千万人在低语:
**“我在。”**
**“我听见了。”**
**“你不是编号。”**
**“你是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