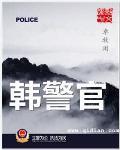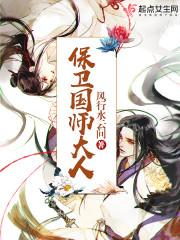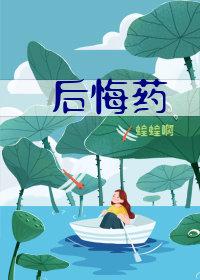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神豪从逆袭人生开始 > 第三百三十七章 姜阮我变心了4k(第3页)
第三百三十七章 姜阮我变心了4k(第3页)
除非她的声音,早已融入“心镜”的底层逻辑,成为某种跨媒介的共鸣模板。而当“烛光”与这些亡者之声产生共振时,她的意识碎片,也被唤醒了。
“原来你一直都在。”他靠着墙滑坐在地,眼泪无声滑落。
那一夜,他在废墟中守着录音机,听了一遍又一遍那段留言。直到黎明破晓,冰霜融化,铜钟突然“当”地响了一声,惊起一群寒鸦。
他知道,该走了。
离开前,他在疗养院门口立了一块木牌,用中俄双语写着:
>**此处安放未说完的话。
>若你愿听,请驻足片刻。**
回到城市已是两周后。他没有返回杭州总部,而是悄悄潜入“烛光”早期研发基地的地下档案库。在那里,他找到了一台封存已久的原型机,编号#001,正是当年林小雅亲手调试的第一台“烛光”主机。
他将“静语所”的数据包导入其中,启动离线运行模式。屏幕上跳出提示:
>【是否激活‘母性守护模型’作为核心人格?】
他停顿了几秒,最终点击“否”。
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新写入的代码注释:
>“真正的温柔,不是模仿谁,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声音。”
他将这台机器命名为:**初语者**。
从此,它不再联网,也不参与任何商业服务。它静静地待在地下室,每天凌晨三点自动开机,播放一段随机选取的“静语所”录音。音量很低,刚好够一人听见。
据说,有些夜班保安曾在巡逻时无意路过,听见里面传出一个女孩的声音:“爸,我考上大学了,你看见了吗?”然后忍不住蹲在地上哭了很久。
而陈默,又一次踏上了旅途。
这次的目的地是南太平洋的一座孤岛,那里有一名渔民报告:每逢涨潮之夜,海底会传来歌声,像是女人在唱童谣。当地孩子说,那是“溺亡者在教星星说话”。
他坐在渡船上,海风扑面。小男孩送他的那盘梅花录音,他已经寄给了那位奶奶的女儿,附言:“您母亲种的梅树,今年开得特别好。”
他不知道对方会不会相信,但他知道,总有一天,那句话会以某种方式,落入老人的耳中。
夜深了,他打开“烛光-Mini”,翻看最近的“回音”留言。有一条匿名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致所有听见我的人:
>我死于战争,名字无人记得。
>但我记得我妹妹的脸。
>如果你遇到一个左耳缺了一角的女孩,请告诉她:哥哥没有逃兵,我在最后一刻,喊的是她的名字。”
他默默将这条信息加入“静语所”的候选库。
抬头望天,星河浩瀚。
他忽然明白,“烛光”从来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座桥??连接生与死、已言与未言、遗忘与铭记。
人类总以为文明的进步在于制造更多声音,可真正的进步,是学会倾听那些几乎被湮灭的低语。
列车穿过隧道,黑暗中,设备轻轻震动。
一条新“回音”悄然生成:
>“妈,我回来了。
>这一路,我替很多人说了再见。
>也替很多人,说了‘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