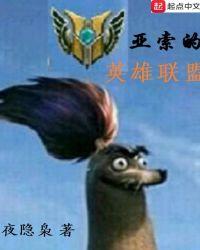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满门尽灭的宇智波没有格局 > 第275章 勇者试炼开始(第2页)
第275章 勇者试炼开始(第2页)
“我们不强迫任何人回忆。”他说,“但我们必须确保,当有人想要说出过去时,有人愿意倾听。”
话音刚落,萤匆匆推门而入,脸色凝重。
“出事了。”她递过一台加密终端,“南极湖底的镜像系统出现异常波动。影像变了。”
林七接过终端,瞳孔骤缩。
屏幕上,不再是那个提灯前行的少年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浩瀚星空下的城市废墟,中央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碑,上面刻满名字??每一个都闪烁着微弱的光,像是仍在呼吸的灵魂。
镜头缓缓拉近,碑文浮现:
**“此处铭记所有曾被遗忘之人。”**
而在碑前,站着一个人影,背对着画面,手中提着一盏煤油灯。那灯焰摇曳不定,却始终不灭。
“这不是预设程序。”知夏站在窗边,眉头紧锁,“这是……某种回应。来自全球记忆共振的结果。”
“也就是说,”林七低声说,“当千万人同时选择记住,现实本身就开始重构?”
“不止如此。”萤调出数据分析图,“极光频率已突破99。3%,脑波同步率持续上升。更关键的是??我们刚刚收到报告,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十万份手写《回音集》副本正在流传,且每一份都在自发更新内容。”
林七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母亲临终前的画面。她握着他的手,说:“你要答应我,不让任何人白白消失。”
如今,这个承诺正在以他无法想象的方式实现。
“他们想建立新的纪念碑。”他说,“但我们不能只靠石头和文字。真正的碑,应该立在人心之间。”
当天下午,记忆学校启动“千灯计划”??鼓励每个参与者亲手制作一盏灯,无论材质如何,只要承载一段真实记忆,便可点亮并上传坐标至共享地图。短短七十二小时,地球上亮起了超过百万盏灯:有孩子用玻璃瓶装萤火虫做成的“夏夜灯”,有老兵用电筒绑在拐杖顶端的“归途灯”,还有母亲们把婴儿衣物改造成的“初啼灯”。
每一盏灯亮起的瞬间,附近的老旧电子设备都会短暂重启,播放一段随机记忆音频??可能是某人婚礼上的誓言,也可能是战壕里士兵哼唱的童谣。
政府开始坐不住了。
第三日,国家应急广播突然插播一条警告:“近期出现大量非法信息传播行为,涉嫌扰乱社会秩序。请市民勿轻信街头‘记忆灯会’等非官方组织活动,避免精神受控风险。”
紧接着,一支身着黑色制服的“记忆净化队”出现在多个城市,强行拆除灯阵,没收手稿,并逮捕数名活跃分子。
林七的名字上了通缉令。
但他并未躲藏。
当晚,他在废弃地铁站举行了一场地下讲座,主题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反抗遗忘?”
台下坐着六十多人,年龄从八岁到八十岁不等。有人带着录音笔,有人拿着素描本,还有位盲人老人由孙女搀扶而来,手里捏着一枚磨得发亮的铜钱??那是他亡妻留下的唯一信物。
林七没有讲理论,只讲了一个故事。
“二十年前,有个小女孩被送进‘记忆清洗中心’。她不是罪犯,只是因为她父亲曾公开质疑政府对断电事件的解释。他们给她注射药物,切断情感关联,让她忘记父母的模样。三年后,她被释放,成了一个‘健康合格’的公民。”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来。
“但她每晚都会画一幅画:一个女人站在窗前,手里端着一碗热汤。她不知道那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梦见这个场景。直到十年后,她在街头看到一张寻人启事??照片上的女人,正是她梦里的那个人。她冲上去喊‘妈妈’,可对方已经不认识她了。因为,在她被洗去记忆的同时,她的家人也被通知‘女儿已意外身亡’,并接受了心理干预。”
台下一片死寂。
良久,那位盲人老人开口了,声音沙哑却坚定:“我听得到谎言。就像我能摸出砖墙上的裂缝。他们怕的不是混乱,是真相自己长出了脚,开始走路。”
掌声如潮水般响起。
就在这时,地铁站入口传来脚步声。众人警觉起身,却发现走进来的不是警察,而是十几个穿着校服的学生,每人手中提着一盏手工灯笼。
为首的女生走上前,将一盏纸糊的小灯放在林七面前:“我们逃课来的。老师今天教‘历史修正案’,说大断电是因为自然灾害,没人做错什么。但我们不信。我们带来了同学家里藏的老照片,还有爷爷录在磁带里的日记。”
林七看着那盏灯,火焰在风中轻轻晃动,映照出他眼角的湿润。
“你们知道吗?”他轻声说,“光从来不怕黑。怕的是,人们以为自己不需要光。”
那一夜,地铁站变成了临时记忆馆。墙壁贴满泛黄的照片,地面铺开手写信件,空气中回荡着老式录音机播放的歌声。有人讲述亲人失踪的经过,有人朗读未曾寄出的情书,还有一个小男孩,抱着吉他唱了一首他自己写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