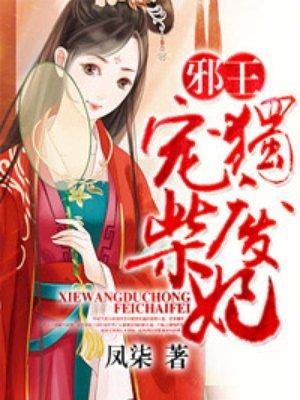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新罕布什尔旅馆 > 第十二章 鼠王综合征最后一家(第4页)
第十二章 鼠王综合征最后一家(第4页)
“我觉得他们选来演你的那个笨蛋,”弗兰妮告诉我,“身上一点生机活力都没有,只会傻里傻气地装可爱。”
“呃,我不知道,不过,你有时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弗兰克取笑我说。
“就像一个老阿姨、一个老处女在那里举重。”莉莉对我说,“他们把你演成了那么个人。”
在第三家新罕布什尔旅馆照顾我父亲的头几年里,大部分时间我就觉得自己成了这么个人:一个举重的老阿姨、老处女。从维也纳得了美国文学学位的我,现在成了父亲的幻想的看管人,说起来倒也是一个不错的事。
“你需要一个好女人。”弗兰妮在电话里对我说——从纽约,从洛杉矶,她不断打来长途电话,她现在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了。
弗兰克跟她争论说,或许我更需要一个好男人。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很谨慎的。我很高兴能帮助父亲创建一个梦幻的世界。那个悲观绝望的菲尔格伯特创立了一个很好的传统,现在我遵循她的做法,一到晚上就为父亲念书。我特别喜欢为父亲念书——为别人大声朗读成了我在这个世间最快意的一件事情。我还成功地激发了父亲对举重的兴趣。不是只有眼睛好好的人才能举重。现在,我和父亲在那个旧舞厅里度过无数个愉快的早晨。我们在舞厅的各个地方都铺上垫子,放上适合做卧推的凳子。每次我们都准备好各种杠铃和哑铃——从舞厅往外看,大西洋的壮丽景色尽收眼底。当然,父亲是没有办法看到美景的——他静静地躺在垫子上,感受海风拂过他的身体,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前面说过了,自从抱死了阿尔拜特之后,我就不怎么举很重的杠铃了,父亲现在也算是一个老练的举重运动员,他发现了我的这一情况。为此他也责备过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只喜欢做些轻量级的举重项目。那些重量级项目,我现在都让父亲做。
“噢,我知道你的身体状况依然是不错的,”他带着嘲笑的口气对我说,“可是你无法与一九六四年夏天的你相提并论了。”
“人不可能一辈子都活在二十二岁。”我提醒他说。我们一起举啊举,一连举了好一阵。在缅因州,在这样的早晨——大雾还没有完全散去,大海的湿气包裹着我们的身体——我不禁想象起自己当年刚开始举重的那个场景——想象自己躺在索罗以前特别喜欢躺的那块地毯上,艾奥瓦鲍勃在我身边指导着我,而不是像现在,我在指导我父亲。
等时光把我悄悄晃到四十岁,我才想着要找一个女人一起生活。
我三十岁生日的那一天,莉莉给我寄来了唐纳德·贾斯蒂斯的一首诗。
她很喜欢那首诗的结尾部分,认为这个结尾非常适合我。我当时很不高兴,马上写了几句话给莉莉寄去:“这位唐纳德·贾斯蒂斯是何方神圣?难道他说什么都适合于我们?”不过,对于任何一首诗来说,这都是一个很好的结尾——在三十岁的时候,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今天三十了,
我看见树林闪着光飞过,
就像蛋糕上的蜡烛,
就像太阳下山,
一道亮光刹那间闪过,
可是,在黑暗来临之前,
我们还有时间许愿,
但愿我知道该许什么愿,
以前我或许知道,
俯身在干净的
被烛光照亮的桌布上,
一口气把蜡烛全部吹灭。
等弗兰克四十岁的时候,我要给他寄去我的生日祝贺,里面附上唐纳德·贾斯蒂斯的一首诗《男人四十》。
男人四十
学会轻轻地关上门
那些房间
他们再也无法回去
弗兰克很快给我寄来了简短的回信——他说他再也不要读那该死的诗了。“关上你自己的门吧!”弗兰克气呼呼地写道,“你很快也四十了。至于我,我砰的一声关上那该死的门,以后什么时候想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好样的,弗兰克!我想。他总是不停地走过开着的窗户,没有一点害怕的意思。所有伟大的经纪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让那些最不可思议、最不合逻辑的建议听起来合情合理,他们让你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这样你才能得偿所愿,或多或少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不管怎么样,总是能得到一些东西。你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勇猛地冲进黑暗——好像一个世上最高明的人在指点你——你这样做,到最后至少是不会一无所获的。谁会想到弗兰克最后会变得如此可爱呢?(他可是一个坏透了的孩子。)弗兰克把莉莉逼得如此之紧,我并不怪他。“紧逼莉莉的,”弗兰妮总是说,“是莉莉自己。”
那些该死的评论家喜欢上了莉莉的《我要长大》——他们屈尊俯就地盛赞莉莉,说不管这个作者原先是多么无名,现在看来,出身于挽救了维也纳歌剧院的这个著名家庭的这位莉莉·贝瑞小姐,还是“一位不错的作家”,真可谓“前途无量”。他们大吹特吹,说莉莉的文笔是多么清新自然——所有这些评论对莉莉意味着,她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她只能一路向前,她只能把写作当作一件严肃的事来做。
我们的小莉莉写这第一本小说,几乎出于偶然。她写那本小说,只是想用这个委婉的方式表示她要长大。但是,现在外界都说莉莉是一个作家了,其实她或许至多不过是一个心思敏感、热爱文学的读者,只是觉得自己想写点什么而已。我想,最终害死莉莉的,正是这写作,因为写作是可以杀人的。写作耗尽了她的心血。她的个头不够大,经不起这样的自我虐待,经不起这样不断地自我消耗。《我要长大》这部电影上映后,弗兰妮声名大噪,而电视连续剧《第一家新罕布什尔旅馆》播出后,又让莉莉·贝瑞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但我想,莉莉其实只想写作,她不想要别的——我们总是听作家这样说。我想,她现在只是静下来自由自在地写作。但问题是,莉莉的第二本小说写得不怎么好。这第二本小说名为《心灵的夜晚》,取自她崇拜的导师唐纳德·贾斯蒂斯的一行诗:
心灵的夜晚终于来了。
萤火虫在血泊中抽搐。
下面还有几行。其实,如果她更明智些的话,应该选用唐纳德·贾斯蒂斯的另一行诗作为她第二本小说的书名:
弯着弓计算着什么时候射出这支定然失败的箭。
她本该起《定然失败》这个书名,因为这第二本小说就是一个失败。这是一个她无法处理的题材,这个题材对她来说太难了。她写的是梦想的死亡,写梦想如何艰难地死去。这是一本勇敢的小说,与莉莉小小的自传没有直接关联,与她自己的生活相去甚远,她写了一个她根本无法把握的陌生国家——这是一本含糊其词的小说,可以看出她笔下的文字对她自己来说也是极其的陌生。当你用模糊的语言写作时,你总是变得很脆弱。当那些评论家,那些该死的评论家用枯燥乏味、油腔滑调的语言不急不缓地批评她时,她就很容易受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