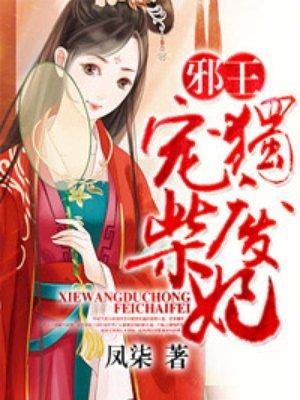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毛姆短篇小说全集(全二十二册) > 异国谷物(第4页)
异国谷物(第4页)
“很抱歉,乔治周三不能来吃午饭了。”
“那周五呢?”
“周五也来不了,”我觉得也没必要绕圈子,“事实上是他家人不太想让他和你共进午餐。”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阵儿才开口:
“我明白了,行,你周三那天还是会过来吧?”
“我当然会过去。”我回答道。
就这样,在周三下午一点半的时候,我漫步到了柯曾大街。菲尔迪热情周到地接待了我,殷勤中带着些许做作,这是他不自觉养成的习惯。他没有提布兰德一家。一起坐在客厅时,我不由得感叹这家人都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以如今的审美来看,这个房间稍显拥挤,摆在玻璃橱窗里的鼻烟盒和法国瓷器虽然不太合我的口味,但无疑都是上等品;那套路易十五时期的家具,配上精美斜针绣绣品,肯定价值不菲。我对墙上挂着的朗克雷、佩特、华托[20]的画作兴趣不大,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些都是难得的佳作。这样的布置对这位饱经世事的老人而言倒也合适,也符合他那个年代的风格。门突然打开了,仆人宣布乔治到了。看着我惊讶的样子,菲尔迪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很高兴你终究还是来了。”他一边和乔治握手一边说道。
我看到他偷偷扫了一眼他这位第一次见面的外甥孙。乔治那天的穿着很讲究——黑色的短外套配上条纹裤子,再加上当时最流行的双排扣黑色马甲。只有个子高高瘦瘦、肚子微微凹陷的人才能将这身衣服穿出优雅感。我确定菲尔迪肯定知道乔治请的是哪一位裁缝,去哪家饰品店,也认同乔治的品位。乔治仪表堂堂、身材匀称,加上穿得又这么漂亮,看上去自然格外英俊。我们起身下楼去吃午饭。菲尔迪在这种社交场上自然游刃有余,很快就让乔治放松了下来,不过看得出菲尔迪也在仔细打量这个小伙子。接着,不知道为什么,菲尔迪开始讲那些犹太故事,讲得津津有味,模仿得惟妙惟肖。我看到乔治脸都红了,虽然也在笑,但笑容里充满了尴尬。我不知道是什么引得菲尔迪这么冒失。他就看着乔治,讲了一个又一个犹太故事,就好像永远不会停下来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某个我不了解的原因,不然菲尔迪为何故意让这个年轻人感到窘迫,并从中获得一种恶意的快感。后来我们回到了楼上,为了缓和气氛,我邀请菲尔迪为我们弹奏钢琴曲。菲尔迪弹奏了三四首华尔兹舞曲,指法一如当年那般轻盈,曲调也恰似当年那般欢快。接着他转身看向乔治。
“会弹钢琴吗?”他问。
“会一点儿。”
“要不要来弹一曲?”
“可是我只会弹古典乐,估计你也没有什么兴趣。”
菲尔迪微微笑了笑,没有坚持。这时我表示自己是时候告辞了,乔治随我一起离开了。
“好一个恶心的犹太老头,”我们刚走到街上,他就说,“我真讨厌他讲的那些故事。”
“那可是他的看家本领,每次都会表演一番。”
“如果你是犹太人,你会这样做吗?”
我耸了耸肩。
“话说你最后怎么还是过来吃午饭了呢?”我问乔治。
他咯咯地笑了笑。这是一个无忧无虑、有幽默感的年轻人,就算被舅公惹得有些恼火了,也很快就摆脱了这种情绪。
“他去见了我奶奶。你应该还没见过我奶奶,是吧?”
“没见过。”
“她现在还把爸爸当成在伊顿上学的小屁孩儿。奶奶说我应该和舅公菲尔迪一起吃顿午饭,我们家奶奶说了算。”
“我明白了。”
在一两周后,乔治去了慕尼黑学德语。我碰巧也出了趟远门,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回到伦敦。回来后不久,在一次晚宴上,我发现缪丽尔·布兰德就坐在旁边,于是问了问乔治的近况。
“他还在德国。”她说。
“我在报纸上看到,为了庆祝乔治成年,你们打算在蒂尔比举办一场盛大的招待会。”
“就是设宴招待一下佃户,好让他们认识一下乔治。”
缪丽尔不像平时那么充满活力,不过我也没太在意,她一直是个大忙人,可能是累了。我知道她喜欢聊自己的儿子,便继续说:
“乔治在德国应该过得很不错吧?”
她一直没吭声,于是我瞄了她一眼,惊讶地发现她眼里满是泪水。
“只怕乔治是疯了。”她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阵子都愁坏了,弗雷迪大发雷霆,甚至提都不愿意提起这件事情。我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第一个出现在我脑海里的念头,自然是乔治跟被送去德国学语言的英国青年一样,他们大多住在寄宿家庭里,爱上了那家的女儿,想娶她为妻。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告诉我,布兰德夫妇肯定是要为乔治挑选一个家世相当的妻子。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我问。
“他想当钢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