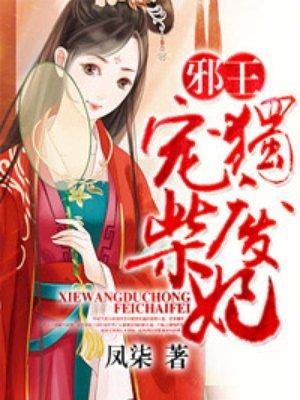皮皮小说网>毛姆短篇小说全集(全二十二册) > 异国谷物(第5页)
异国谷物(第5页)
“当什么?”
“当一名职业钢琴家。”
“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天知道。之前一点儿征兆都没有,大家都以为他在忙着准备考试。后来我过去看望他,只想着他应该一切都好。天哪,以前那么光鲜亮丽的一个人,如今可都成什么样子了,我差点儿都哭了。他说他不会去参加考试,一开始就没这个打算。他之所以提出要学外交,就是想让我们把他送到德国,这样他就能学音乐了。”
“他有这方面的天赋吗?”
“这不重要,就算他有帕岱莱夫斯基[21]那样的天赋,我们也不可能让他去全国各地办钢琴演奏会。我是一个有艺术品位的人,弗雷迪也一样,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我们都热爱音乐,也结交了许多艺术家,但乔治以后是干大事的人,不可能去当一名钢琴家。我们一心只想让他进议会,总有一天他会很有钱,到时候没有什么他得不到的东西。”
“当然说了,可他只是一笑了之。我说他的父亲会心碎的,他说父亲还可以依靠哈里。我当然也爱哈里,那孩子是个机灵鬼,但我们都知道他以后是要接手家族生意,就算都是儿子,我也清楚哈里其实不具备乔治拥有的那些优势。你知道乔治是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只要父亲能每周给他五英镑的生活费,他可以把一切都留给哈里,让哈里来当继承人,所有的一切,包括准男爵爵位都让给哈里。这实在太荒唐了。他说既然罗马尼亚的王储连王位都可以放弃,[22]那他自然也可以放弃准男爵的爵位。可他就是不能这么做,他无论如何都会是第三代准男爵。如果弗雷迪被授予了贵族爵位,那在他去世后也只会由乔治来继承。你知道吗,乔治甚至想换掉布兰德这个姓氏,改成一个可怕的德国姓氏。”
我忍不住问了问是哪个德国姓氏。
“好像是布莱克格尔。”她说。
这个名字我有印象,我记得菲尔迪曾跟我说过,汉娜·拉本斯坦嫁给了阿尔方斯·布莱克格尔,那人后来成了阿尔弗雷德·布兰德爵士,也就是第一代准男爵。这件事情太奇怪了。我很好奇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那个有魅力的典型英国式男孩儿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回家后我自然将这一切都告诉了弗雷迪,他气坏了,我从没见过他这么生气,骂得唾沫星子横飞。他发电报让乔治立刻回来,但乔治回电报说他要忙工作回不来。”
“他在工作?”
“从早做到晚。这也是最让人生气的地方,他这辈子都没干过什么活儿,弗雷迪以前常常说他生来就是享福的。”
“嗯。”
“接着弗雷迪又发了封电报,说乔治如果不回来,就会停了他的生活费。乔治回了封电报说‘那就停吧’。这句话就像是最后一根稻草。你不知道弗雷迪真生气了会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弗雷迪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也知道他让这笔财产增长了不少。我能想象得到,在这位蒂尔比乡绅和蔼可亲的外表下,一定藏着一副冷酷无情的企业家面孔。他已经习惯了凡事都按自己的心意来,我相信他一旦被惹毛了,肯定会变得强硬而冷酷。
“在此之前,我们每次都会给乔治一大笔生活费,但你也知道这孩子向来有多挥霍。我们都觉得他坚持不了多久,事实也是如此,不到一个月他就写信给菲尔迪,说要借一百英镑。菲尔迪找到了我的婆婆,你知道,也就是他姐姐,问她这是怎么了。虽然已经有二十年没说过话了,但弗雷迪还是去见了菲尔迪,求他一分钱都不要借给乔治,菲尔迪答应了。我都不知道乔治这段时间是怎么维持生计的。我知道弗雷迪这样做没错,但我就是忍不住会担心。要不是亲口向弗雷迪保证过,我肯定会在信封里偷偷塞几张钞票,以防有什么意外。我的意思,他万一正在饿肚子呢,光是想想就觉得可怕。”
“你知道吗,如今还有一个大麻烦。我们为他的成年礼做了各种准备,几百张请帖都发出去了。可乔治突然说他不回来了,我整个人都乱了。我写了信,发了电报,要不是弗雷迪不许,我早就跑到德国去了。事实上,我已经算是低声下气地在求他了,求他不要让我们陷入那么难堪的境地。我的意思是,出了这样的事情不好跟人解释。这时我婆婆出手了。你还不认识她吧?那可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太太,你绝对想不到她竟然是弗雷迪的母亲。她原来是德国人,不过家境不错。”
“是吗?”
“说实话我都有点儿怕她。她和弗雷迪商讨了一番,然后亲自写了封信给乔治。信上说,要是乔治能回家过自己的二十一岁生日,她就会为他还掉在慕尼黑欠下的所有债务,而且全家人都会耐心地听他说说自己的想法。乔治同意了,下周就回来,只是不知道具体是哪天。但实话跟你说,我对此并不是很期待。”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晚宴过后众人上了楼,弗雷迪也和我聊了聊:
“我看到缪丽尔跟你说了乔治的事情。那个该死的臭小子!我对他已经没有耐心了,他竟然想把弹钢琴当职业,简直一点儿绅士风度都没有。”
“你也知道,他还很年轻。”我安慰道。
“他以前生活得太轻松了,是我太惯着他,他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回就要让他吃吃苦头。”
布兰德一家在做宣传时向来谨言慎行,我从报纸上了解到,他们按照英国乡绅家庭的习惯,在蒂尔比为乔治举办了一场二十一岁的生日宴会。在那场宴会上,贵族们参加舞会,佃户们则在草坪上的帐篷里边吃点心边跳舞。乐队是专门从伦敦请来的,耗资不菲。画报上的照片是乔治被家人簇拥在中间,手上展示的是佃户们送给他的银质茶具。他们原本打算请画师为乔治画一幅肖像画,但因为乔治人不在国内,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于是就将礼物替换成了茶具。我在八卦记者写的专栏上看到,乔治的父亲送了他一匹猎狐马,母亲送了一台可以自动更换唱片的留声机,奶奶布兰德夫人送的是一套《大英百科全书》,舅公菲尔迪·拉本斯坦送的是佩莱格里诺·达·蒙德纳画的《圣母与圣子》。不难发现这些礼物都很笨重,也没法轻易兑换成现金。既然菲尔迪也出现在那场宴会上,我可以断定乔治这次的怪异行为,促进了父亲和舅公的和解。我猜得没错,菲尔迪一点儿也不想让自己的外甥孙成为一名职业钢琴家。只要一有迹象表明家族荣誉可能要受到损害,整个家族都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对抗乔治的阵线。因为我当时不在现场,只能通过零零碎碎的消息来推断生日宴会结束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菲尔迪告诉了我一些事情,缪丽尔也说了一些事情,后来又听乔治描述了那天的情况。布兰德夫妇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等乔治回到家,重新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周围都是荣耀和光辉,他也就再次亲身体会到能继承这样一份产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到时他自然就会让步了。于是他们开始用爱感化乔治,处处迎合他的心意,对他说的话视若珍宝。他们觉得只要对乔治关怀备至,那么按照乔治善良的性格,他就狠不下心来伤害他们。他们似乎都认定了乔治不想再回到德国,言谈间都在筹划他的未来。乔治的话不多,心情似乎也不错。他在家也没有碰过钢琴,事情看上去进展不错。这个近来冲突不断的家庭终于又恢复了平静。接下来有一天在吃午饭时,聊起了下周全家人都受邀去参加的那场花园派对,这时乔治愉快地说道:
“乔治,为什么不去呢?”他母亲问道。
“我必须回去工作了。我周一出发去慕尼黑。”
气氛顿时安静得可怕。每个人都想找点儿话说,但又怕说错话,众人最终也没有打破这个沉默的局面,午餐在一片寂静中结束了。随后乔治去了花园,其他人包括布兰德老夫人、菲尔迪、缪丽尔和阿道弗斯爵士,则回到了早餐室,他们要开一个家庭会议。缪丽尔哭了,弗雷迪气得暴跳如雷。不一会儿他们听到有人在客厅弹奏肖邦的夜曲,那人自然是乔治。这就好像既然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热爱的乐器来获得慰藉、平静和力量。弗雷迪猛地站了起来。
“把那个噪声给我停下来,”他大吼道,“我是不可能让他在我房子里弹钢琴的。”
缪丽尔摇铃唤来一位仆人,让他去传一句话。
“告诉布兰德先生,老夫人头疼得厉害,可以的话请他不要弹钢琴了。”
最后他们让老于世故的菲尔迪去和乔治聊一聊,只要乔治愿意放弃成为钢琴家的想法,菲尔迪就有权做出某些承诺。如果乔治不愿意从事外交工作,弗雷迪也不会强迫他,但只要他肯竞选议员,家里会负担所有的竞选费用,还会在伦敦给他安排一套公寓,然后每年提供五千英镑的生活费。不得不说这提议确实很慷慨。不知道菲尔迪是怎么跟那位年轻人说的,估计是在描述拥有这样一笔收入的年轻人在伦敦可以过什么样的日子,我相信菲尔迪肯定将那一切描述得十分诱人,但最后还是徒劳无功。乔治只要求他们不要打扰他,每周给他五英镑,让他可以继续自己的学业。他一点儿都不在意日后能够到达什么样的地位,他不想打猎,不想射击,不想成为国会议员和百万富翁,不想成为准男爵,也不想当一名贵族。菲尔迪碰了一鼻子灰,一时恼怒不已。
晚餐后,众人又陷入了激烈的争论。弗雷迪是个急性子,习惯了他人的顺从,这次他向乔治展示了自己说话毫不客气的那一面。我猜他当时举止肯定非常粗暴,试图对他的粗暴加以阻止的女士也被他凶得不敢吭声。这或许是弗雷迪生平第一次忤逆他的母亲。乔治没有妥协,一直沉着脸不说话。他已经下定了决心,父亲喜不喜欢都不重要。弗雷迪当时很专横,不许乔治回德国。乔治则回答说他已经二十一岁了,凡事可以由自己做主,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弗雷迪发誓一分钱也不会给他。
“没问题,钱我可以自己挣。”
“就凭你!你这辈子干过什么活儿?你打算怎么挣钱?”
“把旧衣服卖了。”乔治咧嘴一笑。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气,被吓了一跳的缪丽尔甚至说出了一句蠢话: